| 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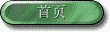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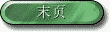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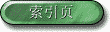
|
第一章 查考书籍的工具书
查考书籍的工具书,主要指各类书目而言。书目即图书目录的简称。它一般只记载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项目,有的兼详图书的流传情况、主要内容与优缺点,以及书籍的真伪和文字的讹误等问题。所以,不论何种形式的书目,除了便于读者查我图书和利用图书以外,也还具有揭示图书内容、宣传图书和指导阅读等重要作用。因此,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指出,目录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是极其鲜明的。那种认为目录学只是提供便利的讲法是不对的,至少是片面的。 现就我国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以及怎样查找各类书籍的方法,分别介绍如下。
第一节 我国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
一、我国书籍的发生和发展
要讲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首先得介绍一下我国书籍的发生和发展的简单历史。因为书目是随着书籍的发生、发展而产生与发展的。离开书籍发展这个前提,就没有书目和图书分类可言。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距今四千多年的夏代,我国已有了典籍。由于目前尚没有充分的实物作为佐证,夏代的事就暂时不去讲它。 《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吕氏春秋·先识览》:“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 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这说明商代已有典籍。商代已有典籍,除了上引资料外,还有没有其它证明?有。甲骨卜辞有“爯册”、“祝册”、“工典”等文字,册作■、■,象以丝绳或皮革贯穿简牍为一束的形状;典字作■,象两手捧册之形。金文册字与甲骨文略同,典字或作■,象简册阁置于■上。汉许慎《说文解字》:“■……从■,在兀上尊阁之也。”又:“■,古文典,从竹。”另外,从记载和实物都证明商代已有书写典籍的工具和材料,例如笔和竹帛之类。不过,由于简牍比甲骨更难保存,所以商代的这种典籍至今未能发现。 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文,近年于周原发现的西周初年的甲骨文,主要是商周王室的占卜记录,刻写于龟甲兽骨之上;商周的金文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最初字数很少,至西周逐渐增多,其中如《毛公鼎》铭文近五百字左右,多属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有关的纪事,史料价值很高,但还不能算是正式的书籍。 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尚书》,主要记周代的历史,其中有《商书》五篇,据学者考定,仅《盘庚篇》是商代的作品,其余都是后人的追叙。 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典籍,据说已日益增多,并且有了专门管理典籍的官吏和藏书的府库。可惜当时的书籍多半已经佚失了。今天见到的《尚书》、《诗经》、《春秋》等等,是经过辗转流传保存至今的少数珍贵著作。 从商代到春秋末年,正处于奴隶社会所谓“学在官府”的时期,文化教育由统治阶级中少数人所垄断,私人著书立说的情况基本上还没有发生。所以,当时的所谓书籍,实际上仅是政府的文告等档案资料的汇编而已。从录写材料来说,或甲骨,或青铜器,或石头、竹签、木片等等,也还没有固定。总言之,这是我国书籍的发生时期,在书籍发展史上属于初期阶段。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冶铁事业的发展,铁器工具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又因牛耕的普及、水利的发达和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手工业、商业也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这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就引起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大变革。这时候,旧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平民和奴隶主的矛盾日益尖锐,新兴地主阶级便利用奴隶暴动、平民斗争等力量,向奴隶主贵族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首先在三晋、齐鲁等国先后建立了地主政权,以后秦楚燕等诸侯国家也普遍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表现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就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各阶级的代言人,纷纷著书立说,各自为本阶级争取政治、经济和文化学术地位而大造舆论,《墨子·天志上》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对图书发展事业一度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汉初,“广开献书”之路,许多门类的著作物又相继产生。直到东汉时期,基本上仍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社会的经济、文化继续有所发展,书籍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战国至两汉,竹木制的简策,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虽然在战国时代出现了帛书,在后汉又出现了纸书,但简策一直居于主要地位。因此,这一个时期可以称为书籍发展史上的简策时期。 《墨子》一书常讲“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也讲“先王寄理于竹帛”。甲骨、金、石用以刻字,竹、帛用以书写,正是先秦以来实际情况的反映。古书上说的“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秦始皇规定每天批阅文书一石(一百二十斤,合今六十斤),都是简牍。我国历史上关于这类文书曾有几次大的发现:第一次是汉武帝末年鲁恭王破坏孔子旧宅,发现战国时代人用古文(所谓“蝌蚪文”)抄写的《尚书》、《■礼》、《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每简二十字到二十五字,与当时通行的隶书(称今文)不同,有人相信有人怀疑,从而引起了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第二次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有一个名叫不准的人盗发战国魏襄王的坟墓,因而发现十几万根竹简,后经荀勗、束皙、和峤等整理,共得《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十六部古书。每简长二尺四寸,四十字,墨写,用素丝编连。此后清光绪末年英人斯坦因于新疆、甘肃一带所得汉魏简牍文书“流沙坠简”,1930年在内蒙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得前汉中期到后汉初期近万根木简,称之为“居延汉简”,皆是公文而非书籍。解放后,1952—53年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古墓中发见了几十根竹简,都是故国时楚国的遗物。1957年在信阳长台关楚墓中又发见了一批,也是战国时楚国的遗物。1959年在武威汉墓发见了五百零四根竹、木简,其中四百六十九根是前汉末年抄写的《仪礼》,计有《乡饮酒》、《丧服》等七篇,每简长二尺四寸。由此证明,古书讲先秦简长二尺四寸,用以写经典、法律和国史,一尺二寸用以写《孝经》等书,八寸写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籍是有一定依据的。秦汉以后,根据王国维的考证,简长有二尺、一尺五寸、一尺、五寸的区别。这些简,或用丝绳,或用皮革编连。《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韦为熟牛皮。孔子晚年反复读《易经》,把穿连竹简的牛皮磨断了三次,这个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古书的面貌和古人刻苦学习的精神。 帛书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直到汉代还应用。帛是一种丝织品,或称缣、素,价值较为昂贵。近几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过这种帛书(如《老子》、《十大经》等)。 从三国到唐末,这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书籍的发展已进入第三阶段,是纸写本盛行的时代。《晋书》记陈寿《三国志》成,时人多爱抄录;左思撰《三都赋》,京师豪贵竞相传抄,一时洛阳为之纸贵,就是纸写本盛行以后的一种反映。近年于新疆发现晋写本《三国志》、唐代卜天寿抄《论语郑注》、唐《西州营名籍》等,都是用的帘纹纸,这又提供了新的例证。 起初,纸书同帛书一样,是卷轴式。纸书逐步代替简策和帛书,到隋唐而达到极盛时期。它的生产方法是手写,虽说雕板印刷于唐代已发明,但尚未推广。《汉书艺文志》著录书籍有篇、卷之分,称篇者为简策,称卷者为帛书,纸写本继承了帛书的形式,所以这个时期亦可称为卷轴时期。 我国是首先发明纸的国家。据考古发现,早在西汉初年就发明了植物纤维纸,扩大生产则要到东汉蔡伦改进、推广以后。但东汉一代,甚至到了三国两晋时期,少数贵族、文士尚有贵素贱纸的风气,南北朝以后纸书才普遍推广。 魏晋时期,由于书籍的发展,公私藏书极为丰富。隋文帝时政府向民间搜求异书,校写完毕,原书归还,并每卷赏绢一匹。政府召集全国字写得好的人抄录书籍,凡三万余卷。唐玄宗时特设修书院,专掌抄校书籍。又佛教自两汉传入,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达到极盛。按照佛教教义,传播佛经功德无量,所以自西晋以来,佛寺和教徒尽力抄写经书,广为流传,而雕板印刷之首先就是从印刷历书和佛经开始,这不是偶然的。 从五代至清代的中英鸦片战争,属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虽然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但在书籍发展史上却是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个历史时期,印刷术成为书籍生产的主要方法,并且有了辉煌的发展。书籍的形式已定型为册叶,并且经过发展而达到线装的形式。1900年敦煌发现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印的《金刚经》,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印刷物。印刷术从我国传播到东方国家,已有更早的实物发现,一为770年左右的日本刻《陀罗尼经》,一为704—751年间新罗刻的《陀罗尼经》。这都足以说明,我国雕板印刷的发明,可以上推到初唐。雕板印刷发明之初,主要印历书和佛经,到五代后唐时宰相冯道建议刻印儒家九经,而于后周时完成,从此各级政府官署都以刻印经史书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这对书籍的刊印出版事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印刷书籍的盛行,印刷术也不断改进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活字印刷术和套色印刷术的发明。北宋仁宗时毕昇发明泥活字,元王祯又创造木活字,使我国印刷事业又从雕板印刷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明代除木活字外,还使用铜活字和锡活字。另外,发明于元末而盛行于明中叶以后的套色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都为我国刻书事业的重大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经过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历程,但我国书籍出版还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传统的手工业印刷术逐步为机械化印刷术所代替,册叶制度虽然还保持着,而书籍的形式已由线装变为平装和精装。这样,书籍印刷过程加快了,书籍形式又改变得更便于阅读和收藏,随着科学门类的日益增多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有所提高,出版书籍的品种和数量,都大大增加起来。当然,其中确有大量好书,但反映这段时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腐朽性的糟粕之类出版物也不少。
二、书目的产生和图书六分法
春秋以前,由于书籍尚处于发生时期,数量有限,当然没有必要编制书目。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学派的崛起,图书的增多,这才使划分学派和依学派而将学术思想或图书进行分类,其中包括编制书目等等工作,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春秋末年,孔子以六艺分科教授学生,可以说是我国进行学术思想分类的开始。《庄子·天下篇》分诸子百家为七派,评论颇有见地。《荀子·正名篇》关于“究名实”、“辨同异”的论述,所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等等,应是我国较早的分类原理。荀况的《非十二子》和汉代的《淮南子·要略》等篇,都对学派进行了具体分类。而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分析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派之特点和相互关系,论述尤为精到,可以说是对先秦以来学术分类的一个总结。所以梁启超说:“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其櫽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釐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八册) 分类学在科学研究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能指导研究的途径,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虽有所不同,但就我国古代来说,二者之间关系至为密切。如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首撰《别录》、《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国家书目,也是我国目录学的真正开创者。刘歆《七略》中的诸子略,即以司马谈所分六家为主类,益以纵横等家,就是很好的证明。 《隋书·经籍志》认为我国目录的体制起源于《诗》、《书》的序:“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见《簿录篇》小序) 《诗》、《书》的序是否孔子所作,这早已成了问题。不过不管怎么说,它和司马迁《史记》、扬雄《法言》的自序一样,分释各篇的旨意,是一种图书的目录,也是我国目录的最早体制之一。 秦始皇焚书时,李斯定下法令: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记》)据姚名达先生《中国目录学史》的意见,这种全国范围的行动,倘若政府没有图书分类目录下达,即没有目录以为纲纪,吏民势将无所适从。所以,仅从这个法令加以分析,也可以推想当时一定有了图书分类目录的编制。 秦末农民大起义,彻底摧毁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史记·萧何传》:“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与秦代焚书相反,汉初采取重视收藏图书的政策,按理来说,也要对图书编目登记,做一些最必要的目录工作。另据《史记》、《汉书》的记载,高祖时尝令萧何次律令,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对有关图书显然要进行审校和整理,这无疑是西汉初年大规模的官校书籍的一个创举。 自文帝、景帝时期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到了武帝时候,国力已相当强盛。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在文化上推行崇儒术、黜百家的方针,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于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当时为配合抗击匈奴等军事上的需要,又让杨仆进一步整理兵书,“纪奏《兵录》”。到了成帝时候,“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完一部书,都由刘向写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给成帝等阅览,所谓“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以上见《汉书·艺文志》)当时曾把这些提要另写一份,汇编成《别录》一书,这便是我国第一部解题式书目。 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受哀帝之命,继续校理群书。他在《别录》的基础上,对序录删繁就简,进一步将全国图书详加分类,编成《七略》一书。前面所说《诗》、《书》的序,乃是一书之目录,杨仆之《兵录》,为兵法一类书籍的总目,《七略》则是校理全国图书而编成的综合性的群书目录。 《七略》有集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集略为后列六略的总序及总目,所以实际上只分六大类。我国古代图书主要有六分法和四分法两大系统,六分法即创始于刘歆的《七略》。 刘向、刘歆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经过选择、校勘、写成定本和分类编目等程序,并且写了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工作是艰巨的,成绩是显著的,特别是《七略》,它不只是一部目录学的巨制,同时也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它们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以当时政府丰富的藏书为先决条件,另方面也是先秦以来有关学术思想分类,校理和序录图书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先秦至西汉中期是我国目录学的萌芽时期,那么西汉末年刘氏父子在校书编目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就标志着我国目录学的正式建立,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目录事业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宋郑樵、清章学诚等对《七略》均有所批评。诚然,《七略》所分类目并非尽善尽美,但初创之际,能有如此成绩,已属难能可贵;不足的地方,后人自应求得不断的改进,而不能苛求于古人! 《别录》二十卷、《七略》七卷,唐代已佚失。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即删改《别录》、《七略》而编成,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著录式书目,也是第一部史志书目。由于史书体裁和篇幅的限制,班固删掉了刘书大量的叙录,又把《集略》分割开来,属于总论性质的列于六略之前,大序小序则分别置于六略及三十八种之后,增加了刘向、扬雄、杜林等人的著作,在细目和具体归类方面有所变通和改进,特别是注明“出”、“省”、“入”若干篇,以示更动之处,态度较为严谨。唐刘知几批评他“因人成事”,然而《别录》、《七略》以及汉代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典籍的状况,均赖班志而可考见其梗概,其功似不可没。清代学者金榜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这当然不光是对《汉书·艺文志》的推崇,而是对刘向以来所建立的目录学的重视和肯定。
三、书目的发展和四部分类法
自《七略》创图书六分法,历东汉、三国基本上沿用不改,可算是我国封建社会目录学的第一个时期,亦即目录学的成立时期。 魏晋之际,由于战乱和政局的波动,地主阶级中间较为普遍的产生一种逃避现实斗争的倾向。反映在文化思想方面,那就是摆脱儒家传统的束缚,促成玄学和佛、道二教的兴盛。在史学方面,因受《史记》、《汉书》的影响,私家修史的风气极为盛行,史部著作明显地增多,其中与“门阀制度”多少相联系的人物传记、氏族谱以及地方志书的大量涌现,尤为突出。文学方面,五言诗的兴起,骈体文的发展,诗文集和文艺理论著作的出现,也突破了诗赋的范围而起了很大的变化。凡此种种,不能不反映到图书分类中来,给编纂目录提出新的课题。 魏秘书郎郑默所制之《中经》,仅仅“考核旧文,删省浮秽”,尚未于《七略》之外另创新的分类法。至晋“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隋书·经籍志》)甲部即《七略》之六艺略,乙部包括诸子、兵书、术数、方技等四略,丙部由六艺中《春秋》类目所附史书扩大而成,丁部即诗赋略,增以图赞和汲冢新发现的古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四部区分图书的分类目录,也是在《七略》体制上加以改进、创新的最初尝试。 此后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更换了乙、丙两部的次第,使甲部纪经书,乙部纪史书,丙部纪子书,丁部纪集部书,由此成为后世四部分类法的永制,为东晋以后十余部官修书目所沿用。 宋王俭撰《七志》,梁阮孝绪综合《七志》和《文德殿四部目录》撰成《七录》,这是官修书目发展的同时,个别学者探索新分类法的典型。《七录》十二卷,分内外篇:内篇是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技术五录;外篇是佛录和道录。《七志》、《七录》等书早已失传,但《七录》序被保留下来,成为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一篇重要文献。另外,由于佛经的增多,道安尝撰《综理众经目录》,其后僧佑增辑成《出三藏记集》。前书佚失,后书保存至今,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目录。 唐宋时期,文化极为发达。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各类图书的出版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也随之发展而演变。 唐魏徵等根据当时政府的藏书,参考了《汉书·艺文志》和《七志》、《七录》等书,把图书删并为四部四十七类,并直接冠以经、史、子、集的名称,编成《隋书·经籍志》。这是我国现存的第二部史志书目。它依班志的体裁且有所补阙,首有总叙一篇,四部有后叙四篇,分类有小序四十篇,道、佛叙二篇,末有后叙一篇,合共四十八篇。它是研究唐以前学术源流及其演变,以及刘宋至隋图书概况的重要文献。 魏晋以来至《隋书·经籍志》所完成的图书四分法,直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为历代公私书目所采用,成为目录学史的主要潮流,这便是我国封建社会目录事业的第二个时期,即目录学的发展时期。 刘知几批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重复”、“汗漫”,认为史书不必撰《艺文志》或《经籍志》,就是撰的话,断代史也不应该兼收前代遗书,所以他的结论是:“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史通·书志篇》)我们今天从查考古代图书的流传和学术的演变来看,当然完全可以责之以“偏激”二字。但从编纂体例包括具体分类来说,无论《汉书·艺文志》还是《隋书·经籍志》,也确实存在不少缺点。刘知几在《六家篇》中,以《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并列为史,《春秋》与《左传》也各为一家而不分主辅,这种“援经入史”的主张恰好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代表的儒家传统思想针锋相对;他在《杂说》、《申左》特别是《疑古》、《惑经》等篇中又对儒家经典多方抨击。凡此种种,使我们多少能领略“必不能去,当变其体”的真意。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他的意见又不无进步意义。 《隋书·经籍志》以后,唐、宋、明、清诸史都有艺文志或经籍志。从汉到宋,各正史艺文志都是根据当时政府藏书而编成,故兼收前代遗书;《明史·艺文志》改为专收一朝之著述,《清史稿·艺文志》仍其旧,这种形式的改变应是受刘知几的影响,但在分类体制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进。 除史志书目外,唐宋以来还出现不少有名的官私书目。官修书目如唐元行冲、殷践犹、毋煚等编的《群书四部录》,毋煚在此基础上单独改编的《古今书录》,北宋王尧臣、欧阳修等编的《崇文总目》等等,都是极有名著作,有些史志书目即以上述书目为蓝本。今三书并佚。私家书目如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有名的解题书目。明清两代私家书目甚多,张廷玉进呈的《明史·艺文志》实即王鸿绪的《明史·艺文志》,而王书即依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删改而成。这些私家书目,分类多依四部,但随着图书的增加,子目变动较大,许多原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在《百川书志》等私家书目中就有所反映。 清乾隆时纪昀等所撰《四库全书总目》,也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期一部最大的图书目录,也是沿用《隋书·经籍志》所开创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一个总结性目录。直到今天一些图书馆关于古籍的分类,仍然受到它的影响。由于它是配合《四库全书》禁毁、删节、窜改古籍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部官修书目,所以在收编《四库全书》时,凡对清王朝统治不利的书籍谓之曰“违碍书籍”而均予禁毁,不准流传,《总目》也不著录。在《总目》凡例中,又规定了这样一条著录原则:“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因此,象王充、王安石、李贽等人的著作倍受诽谤和攻击就不言而喻了。 《四库全书总目》共二百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史部分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十四类;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合共四十四类,六十六个子目。另有总序和小序,有些子目附有简短的按语。它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了解我国古籍的版刻、源流、文字异同以及著者事迹等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年郑樵撰《通志》,其艺文、图谱二略记载了历代书籍和图谱,校雠略则是一篇重要的目录学理论著作。元马端临根据历代官修目录、史志书目和私家书目撰《文献通考·经籍考》,广泛辑录有关图书资料,对各种学术源流和图书的内容得失均有论述,其参考价值又在《通志》之上。 目录之学,目录之书,虽然很早就有,但正式称目录学并指出它的重要性,却始于清乾隆时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该书写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江藩也说:“目录者,本以定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为易学而成功且速矣。吾故尝语人曰:‘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见《师郑堂集》)王鸣盛等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在目录学方面并没有具体的建树。介乎王江二氏之间的章学诚,是清代的进步史学家,也是著名的目录学家。他的《校雠通义》集中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则是他对目录学的总的见解。章学诚关于目录学方面的理论,如提出“互著”、“别裁”之法,以及关于分类方面由《七略》必然发展到四部的进化论,是在我国目录学长期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这份可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批判地继承。
四、近代以来的目录学
“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武装斗争。与此同时,一方面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书报、书目大量发行;另方面,逆时代潮流的旧学书目继续争夺文化阵地,斗争极其复杂。 值得珍视的是,从1852年起,太平天国革命政府随同《太平诏书》、《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官书的颁行,在书前附印了《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向广大官兵宣传指导革命斗争的官书,动员他们学习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政策和革命理想。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它和太平天国官书一起,起到了动员、指导广大官兵和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积极作用。 1875年张之洞督学四川时编了一个《书目答问》,这是旧学书籍的综合性选目,历来被看作指导读书门径的有用的导读书目,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它是以封建主义思想为指导,旨在抵制近代新学而编制的。1893年袁昶增订重刊了龙启瑞的《经籍举要》,这是《书目答问》之后继续诱劝青年学生埋头故纸堆和阻碍新学传播的又一代表作。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韬于1889年编《泰西著述考》,介绍自明末利玛窦起至清初诸来华传教士所著译书籍,目的为了提倡西学,有一些特色。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使中国更加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就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之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也同时高涨,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变法维新的政治改良运动。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西学书目表》,介绍了甲午战争以前二十余年间翻译出版的西书三百多种,并附有《通商以前西人译著各书》,可作为1895年以前二十余年间翻译的西书总目录。1896年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把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书刊介绍到中国,对翻译日本书籍风气的兴起颇有影响。显然,康梁的书目,都是为宣传维新变法作思想准备。 二十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高涨,《苏报》、《民报》上相继开辟了“新书介绍”专栏,着重介绍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图书;《国粹学报》上也设有“介绍遗书栏”,着重介绍有关民族主义思想的旧书。1904年出版的《古越藏书楼书目》,开我国近代图书馆藏书目录的先例。它混合新旧图书为一编,分学、政两部,每部各分二十四类,共三三二个子目,这是创造新的图书分类体制的初步尝试。其后在“五四”前后输入了欧美各国的图书分类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杜威完全用号码代替部类的“十进分类法”。 “五四”时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书目发展的同时,胡适抛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打着“整理国故”的旗号,引诱青年“尊孔读经”,受到鲁迅先生的严厉批判。 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现代图书出版发行事业和宣传革命书刊的书目工作都有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在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文化出版事业的破坏、摧残进行不懈的斗争得来的。而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与迫害和谋杀革命作家、捣毁进步的出版发行机构、推行出版审查制度等罪恶手段相配合,国民党和日伪法西斯政权还发布了一系列的禁书目录,从事文化围剿并妄图以此扼杀革命事业。在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学者和出版机构的努力,也还编印了不少综合性书目、专科书目和索引。如平心的《生活全国总书目》,孙殿起的《贩书偶记》,江苏省国学图书馆编的《图书总目》和《现存书目》,以及郑振铎、阿英、孙楷第等的小说、戏曲、文学目录,胡厚宣的甲骨学目录,朱士嘉的地方志目录,何多源的参考工具书目录等等,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另外,我国学者在试用和改进杜威的“十进分类法”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有1927年以前出版的沈祖荣、胡庆生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陈天鸿的《中外一贯图书分类法》,查修的《清华学校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1928年后则有商务印书馆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施廷镛的《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何日章、袁涌进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皮高品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等十余种,都是仿杜、辅杜以至混合中西的分类法。在目录学理论研究方面同样有较大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不少有名的专著,如: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畺的《目录学讲义》,郑鹤声的《中国史部目录学》,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刘咸炘的《目录学》,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目录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书目工作坚持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服务的方向,成为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旧时代的目录事业已不能同日而语。 《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及各大型图书馆的书目或联合目录、各类专科专题目录的编纂出版,历代艺文志和官私书目以及各种目录学专著的再版重印,对杜威等资产阶级学者的分类法的分析批判,和努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建立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尝试,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目录学教研室在从事“目录学”、“专科目录学”课程建设的同时,积极地进行目录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并且用新的观点编出了《目录学讲义》、《普通目录学讲义》等专著,凡此等等,都使我国的目录事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全国总书目》是全国综合性的国家登记书目,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把《全国新书目》每年汇编起来的作用。1949—54年本分为分类总目录和专门总目录两部分。分类总目录采用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图书分类法,在子目方面有所调整和补充;专门总目录部分根据图书具体情况进行分类。1955年本将人大分类法扩展为十九大类,以后历年又有所修改,1960年增为二十二大类。《全国总书目》记录和反映每年全国出版及发行图书的基本情况,可供出版发行部门、图书馆采购编目等业务部门作参考,也可供广大读者查考图书之用。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也是一个规模巨大而极有意义的工作,1959—62年已出古籍部分1—3册,对于查找现存古书极为有用,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诚是新中国目录事业中的一大成就。最近,国家文物局主持编制善本书目。今后,如能编制一部完整的、以单行本为主体的现存古籍总目,再编制一部完整的近代平装书的目录,那将对学术研究提供更大的便利和产生深远的影响。最近,蔡尚思撰《中国文化史要论》,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该书简要地介绍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若干人物和图书,可视作青年的导读书目。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出版了两部新的图书分类法,已逐步为一些图书馆和藏书单位所采用,它为今后全国图书资料统一分类编目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两部分类法是: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组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5年10月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编辑组编,科学文献出版社1975年6月出版的《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由北京图书馆等三十六个单位参加编纂,于1975年10月正式出版。全书首先总分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部类。进而分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五个基本部类。然后在五个基本部类的基础上编制二十二大类: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B哲学,C社会科学总论,D政治,E军事,F经济,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H语言、文字,I文学,J艺术,K历史、地理,N 自然科学总论,O数理科学和化学,P 天文学、地球科学,Q 生物科学,R医药、卫生,S农业、林业,T工业技术,U交通运输,V航空、宇宙飞行,X环境科学,Z综合性图书。大类下再分小类,共约四万个类目。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只限国内发行)是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试用本)的基础上,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根据科学技术文献资料的需要进行加细和适当修订而成。它可供科技情报单位和图书馆分书、分资料用,同时亦可供科技情报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参考。考虑到全国图书资料统一分类和编目的需要,其编制体系、结构、类目设置和标记符号都与《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试用本)的修订稿相一致,即全书分为二十二个大类,共约四万个类目。但为照顾综合与专业的需要和学科交叉重复等问题,该书在编制过程中适当地采用了交替、参见、复分和组配等方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同时亦增加了一些注释,供分编工作者参考,似较《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更为实用。 总之,它们是最新的适用于全国图书馆和情报资料单位的大型图书分类法,既可供专业人员分书编目作参考,又可供读者熟悉图书分类以利索书之用。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技术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极大提高,可以预期,今后图书出版和目录事业更为迅猛的发展,将是毫无疑问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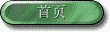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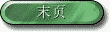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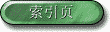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