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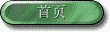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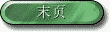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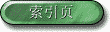
|
第二章 查考字词的工具书
查考字词的工具书,在我国出现较早,汉代所谓“小学”就是文字学,四部分类中的经部也有“小学”。《四库全书总目》把它分为训诂书、字书、韵书三大门。训诂书主要讲字义,字书主要讲字的形体结构,韵书主要讲音韵。现代编制的查考字词的工具书,可分为字典和词典两大类。字典以释字为主,词典以释词为主。实际上,古代的字书大都兼及音义,训诂书也讲字音,韵书也讲字义;现代的字典往往也兼收复词,词典也多以单字为词头,并释其音义,相互间既有区别,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为了使读者对这些工具书有一定的了解,以便遇到查考字词时能选择使用,下面先简述汉字的形体演变和查考字词的工具书的源流,然后分门别类讲述查考字词的途径。
第一节 汉字的形体演变和查考 字词的工具书的源流
一、汉字的形体演变
在不断前进的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不仅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文化,我国文字的发明创造,就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文化的一个贡献,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据考古发现,半坡、姜寨、柳湾、大汶口和城子崖的陶器文字,当是我国文字的雏型,算来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经开始具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特征,若不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水平。 秦始皇统一六国,“取史籀大篆”,“省改”、整理、规范成小篆,而“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种统一文字的政策,既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也符合中央政府的政令贯彻和全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在历史上是进步的。 秦始皇还命程邈对民间的简易书体——隶书,进行了整理,作为小篆的辅助字体。后人为了区别于汉隶,称它为古隶。因为这种字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容易写,到汉代就代替了小篆的地位,成为通用的主要字体。经过长期的使用和改造,汉末它就发展成“熹平一字石经”那样标准化的汉隶。汉代对这种字体还有一种草率的写法称为草书,又称章草,但基本上还是隶书的变体,与晋唐以来的今草、狂草迥然不同。顾炎武曾说:“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故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移,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繇去隶未远故也。”(《日知录·草书》) 魏晋之际又将汉隶进一步改进成楷书,但最初的形体还近于隶书,如魏锺繇、晋王羲之写的字,结体方扁,不同于现行楷书。唐代欧阳询、虞世南等所写的楷书就变成长方型,又经规范才成为“开成石经”那样的写法,楷书才有了定型。在楷书的使用过程中,经过游移和简化成为行书,这两种字体一直通行到现在。 我国文字的演变,就总体而言,其数量是由少到多,而字形则由复杂到简易,这种变化是经过多次改革逐步实现的。除秦代的“书同文”是由统治阶级领导进行的一次文字改革外,此后都是在广泛的实用过程中自行简化,以致约定俗成,改变字形的全貌。 直到本世纪初,又有了文字必需改革的呼声。如1904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表》发表,1907年劳乃宣加以整理,改编为《简字谱录》。此后四十多年,推行注音字母给汉字注音。 1951年,毛泽东同志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8年,周恩来同志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规定了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 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经过分批推行和广泛使用,至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共推行简化字二千 二百三十八个。同时,通过废除异体字,更换部分生僻地名字等,共精简了一千一百多个汉字。1977年底,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规定《草案》第一表的二百四十八个字,即在图书、报刊上试用;在试用一个短时期后,接受群众意见,又停止试用。第二表的六百○五个字,需经过广泛讨论,征求意见,再公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此外,1957年,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还通过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8年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推行。 文字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既要积极,又不能草率。
二、《说文解字》和《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的发展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周宣王时,就产生了我国见于著录的第一部字书《史籀》,也是当时教育儿童的一种识字课本。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配合统一文字的政策,特令李斯等用小篆编撰字书《苍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汉初,民间有人把上述三篇合为一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仍取名《苍颉篇》。以后,陆续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不过,以上这些原只是一般的识字读本,诸如《急就篇》,也是经唐人颜师古作注、宋王应麟补注,才使它具有查考字词的作用。真正奠定了我国古代字书基础的著作,还要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该书以小篆为主体,兼收古文、籀文,全书分为十四篇,收单字九千五百四十三个,用读若法注音,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成五百四十部,创立了按部首收字的体例。它还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六书”理论,创立了较为系统的解释文字的方法,并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代以前的文字训诂,对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晚清以来关于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的研究,正是在《说文解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总之,在我国古代字书史上,它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晋朝吕忱的《字林》,是继承《说文解字》编纂的又一部字书名著。在唐代以前,人们还把它和《说文解字》并称,可惜不久就失传了。据《封氏闻见记》,《字林》的部首与《说文解字》相同,收字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个,较《说文》为多。《魏书·江式传》说,该书“文得正隶,不差篆意”,可见是我国第一部用隶书写成的字书。梁顾野王的《玉篇》,则是我国第一部用楷书编成的字书。今本《玉篇》虽非原本,但可知其对《说文解字》有所增订,也是一本较好的字书。 自隶书、楷书代替篆书通行以后,文字的形体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字和俗体也日益增多,于是就有人注意研究文字的异同,从而产生了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辽释行均的《龙龛手鉴》、宋郭忠恕的《佩觿》及李从周的《字通》。这些字书对于我们认识一个字的异体,辨清许多形体相似的字,还是有用的;其中《字通》创建了按笔画排字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宋代的字书主要有王洙等相继修纂的《类篇》,它继承了《说文解字》和《玉篇》的体例,着重探讨字源,说明文字形体之变化并吸收了大量的新字(共收字三万一千三百十九),讲古音、古训,在字书史上有一定贡献。元戴侗撰《六书故》,改变了《说文解字》的部首编排,分为数、天文、地理、人、动物、植物、工事、杂、疑九部,每部之下各分若干细目,按字义排列。但戴侗攻击许慎用小篆作本字,使人“不知制字之本”,所以他的《六书故》采用钟鼎文字,钟鼎文没有的 字才用小篆。《四库全书总目》曾指出该书“非今非古,颇碍施行”。不过书中解释文字,也有精详的考证,作为研究古代文字训诂的工具书,还是有用的,不能一笔抹杀。 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是我国一部较为通俗而编排方法也比较进步的字书。它收编单字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个,包括俗字,而僻字则一律不收,并把《说文解字》的部首简化成二百十四个,均按笔画多少排列。注音方法是先反切,后直音。对字义的解释,也较为清楚。全书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集,连首卷及附录共十四卷,每卷用表注明各部首及其所在页码,末附检字表以便查找不易辨别部首的字。这种编排方法是字书发展中的一大改进,后世多沿用。该书在明末曾风行一时,给它作补编或用其名新编的字书也很多,其中流传较广的则是张自烈的《正字通》。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张玉书等奉命撰《康熙字典》,这是我国字书第一次用字典的名称。该书继承了《字汇》和《正字通》的体例,分为二百十四部,共收字四万七千○三十五,用反切注音,释义旁征博引,可以说是我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一个高峰。当然,该书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乾隆时王锡侯著《字贯》一书,就对《康熙字典》的错误有所指摘和议论;但因此冒犯了康熙“御定”的威严,又因该书没有“避讳”,落了个作者满门抄斩,其著作也全部被销毁(事见《掌故丛编》)!直到道光七年(1827年),王引之奉皇帝之命,著《字典考证》,才校正了该书引书的错误二千五百八十八条。显然,错误当不限于此。第二节还要介绍清代以后人们的评论,这里从略。 我国古代专门汇集经史中文字训诂的字书有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清阮元的《经籍籑诂》,集释佛经音义的著作有唐释玄应的《一切经音义》、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研究虚字的有清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都是价值较高的专著。
三、《尔雅》等训诂书的兴衰
所谓“训诂”,就是解释词义;解释词义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当代普通话的词语说明古代词、方言词的意义,这叫“诂”;一是说明词的定义和应用范围以及它和同义词、近义词的分别,这叫“训”。 《尔雅》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第一部训诂书,也是我国古代训诂书的代表作。此书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四库全书总目》说:“大抵小学家缀辑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大约该书产生较早,春秋到汉初这一时期内,经过不少人的增补,到汉代才定型。今本《尔雅》按收录词汇的内容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等十九篇。它的内容丰富,不仅涉及到古代的一般词汇,还涉及到古代社会的人事、天文、地理和生物等方面的知识,分门别类进行了解释,是研究和查考先秦词汇的重要资料,在我国语言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部词典成书较早,不少内容若没有后人的解释,也难以看懂。汉代以来,为《尔雅》作注的不少,但大多已失传,现存晋郭璞的注和宋邢昺的疏,即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尔雅注疏》。此外,宋代还有陆佃的《尔雅新义》、郑樵的《尔雅注》,清代研究《尔雅》的著作更多,最著名的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 《尔雅》一书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被列为儒家的经典,对后世训诂书的影响颇大。后世训诂书,有的补充《尔雅》内容,有的仿其体例,且多以“雅”字命名。其中旧题孔鲋的《小尔雅》,是最早的一部补充《尔雅》之作。此后有汉刘熙的《释名》,除对字词进行简单的释义外,并进一步探求语源。魏张揖的《广雅》,则博采群书,以补《尔雅》训诂之缺。宋代补《尔雅》之作有:陆佃的《埤雅》,罗愿的《尔雅翼》。明代朱谋炜的《骈雅》,专门收录冷僻深奥的词汇;方以智的《通雅》,特点在于探讨语源。清代吴玉搢收录形音歧异而意义相同的词,撰为《别雅》;史梦兰集叠字,撰《叠雅》。总之,以上诸“雅”,都是收录古籍书面语言的词典。 我国第一部专门收编各地群众口头语言的词典,当推旧题扬雄撰的《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汉末至晋初的人都说此书是扬雄所作,如应劭的《风俗通义》和常璩的《华阳国志》。但是,《汉书》的《艺文志》和《扬雄传》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所以宋代洪迈便怀疑起来,以为扬雄作《方言》之说出于依托。《四库全书总目》断为“真伪皆无显据”。但该书自问世以后,研究它的名家,颇不乏其人,晋郭璞的《方言注》,更多所阐述,贡献较大,且流传至今,王国维在《书尔雅郭注后》、《书郭注方言后》曾给予分析、比较和肯定。清代学者为《方言》作校勘疏证工作的主要有:戴震的《方言疏证》,钱绎的《方言笺疏》,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但是,集大成之作,还是周祖谟的《方言校笺》(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续《方言》及收编方言俗语的专著还有不少,如:汉服虔的《通俗文》,唐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阙名的《释常谈》、龚颐正的《续释常谈》、李翊《俗呼小录》、明李实的《蜀语》等。 清代续《方言》的著作主要有:杭世骏的《续方言》,程际盛的《续方言补正》;考证一地方言的有: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专集诗词中方言的有:李调元的《方言藻》;专集常言俗语的有: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钱大昭的《迩言》等。
四、《广韵》到《音韵阐微》的变化
我国古代韵书的编纂,是随着汉字音韵的发现和研究而出现的。魏李登的《声类》始分宫、商、角、徵、羽五声,晋吕静的《韵集》除按五声分卷外,又创立了韵部,这两书就是韵书的先驱。此后,齐梁间周颙的《四声切韵》、沈约的《四声谱》,定汉字读音的平、上、去、入四声,为后代韵书奠定了基础。 隋文帝初年,鉴于各地方言中四声分歧较大,“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而以前的韵书缺乏定韵标准,各有错误,于是陆法言与颜之推等在仁寿元年(601年)编成《切韵》。这是综合南北多种语言、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一部重要著作,为其后的《唐韵》甚至宋代的《广韵》所本,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有残卷了。近几十年来,经过研究考证,《切韵》分一百九十三韵,韵目次序不及《广韵》整齐,字数较少,注亦简略。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孙愐据《切韵》增字加注,重加刊定,改名《唐韵》,但原书亦已亡佚。 《广韵》又称《大宋重修广韵》,是陈彭年、丘雍等于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奉诏修,至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增广《切韵》成书。全书分二百○六韵,收录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注文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是我国现存最早和最完整的韵书。它保存了丰富的声韵学材料,文字训诂亦多可取,宋代知识分子即把它当作通用的字典,后人更常把《广韵》、《说文解字》和《尔雅》三书并称,作为我国古代字书中三大系统的代表。以后,丁度等又撰《集韵》,仍分二百零六韵目,韵目名称和次序稍有更动,收字比《广韵》多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为我国收字最多的一部韵书,注文虽不及《广韵》详细,但引证古书材料很可贵,且注重文字的形体和训诂,是研究文字训诂和宋代语言的重要资料。此外,丁度等删取《切韵》编过一部《韵略》,后改名《礼部韵略》,毛晃再把它增补修订为《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即后来所称的《增韵》。 金元间,随着中古后期语言的逐渐发展变化,实际语音与《广韵》的二百零六韵越来越远。金哀宗正大六年(1229年)王文郁撰《平水新刊韵略》,并为一百零六韵;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年)刘渊撰《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归并为一百零七韵;金韩道昭撰《五音集韵》,归并为一百六十韵。此后,元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阴时夫《韵府群玉》分别沿用刘、王韵目,直到明代官修《洪武正韵》,进一步归并为七十六韵。至于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以北音为正音,根据元代北曲用韵,首倡“平分阴阳,入派三声”之说,分十九部。由于该书是适应当时政治中心北移而专门研究北音的,所以也是研究近代以北音为主的普通话语音的重要资料。 清康熙时李光地、王兰生等奉诏撰《音韵阐微》,雍正时完成,全书韵部仍分一百零六。该书《凡例》说:“世传切韵之书,其用法繁而取音难。今依本朝字书合声切法,则用法简而取音易。”于是改革以前韵书的反切方法,并根据当时北方官话来定字的音切。这种读音既非秦汉古音,也非《广韵》系统的中古音,而接近于今天的读音,给我们提供了读音上的方便。
五、近代、现代字典和词典的编纂
近代、现代的字典和词典,是在古代这一类工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华大字典》,编者陆费逵、欧阳溥存等,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全书收单字四万八千余,稍多于《康熙字典》,还纠正了后者的错误二千多条。尽管该书的缺点和错误也不少,但因它收字较多,在新的大型字典出版以前,还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字典。 在词典方面,《辞源》是编辑最早、规模较大的一部。该书由陆尔奎、方毅、傅运森等任编辑,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正编、1931年出版续编,后来又多次重印再版。全书收词目约十万条,内容包括普通语词、成语、典故和人名、地名、书名以及专科术语等等,按字头部首编排,每个字头先用反切注音,并附直音,再标明声韵,解释字义。词条按词头首字排列在字头之后。该书在内容和编排体例上,都吸收了前人的成果,注音简易,词条较多,引证丰富,释义明了,至今仍不失为有使用价值的词典。它的缺点是,第一、文史方面的条目多根据唐宋以来的类书,没有核对原文,往往发生错误和遗漏,而且引书不注篇名,难以查对;第二、摘引原文不标明删节,容易产生断章取义的错误;第三、有的词条去取失当;第四、没有使用新式标点;第五、一些释义上的立场、观点也有问题。 继《辞源》之后的百科性词典应数《辞海》,舒新城、张相等编,1936—1937年由中华书局分三册出版,后又再版。全书收录词条的数量和编制体例大致上与《辞源》相同。当然,《辞海》对《辞源》所存缺点错误有一些改正,如引书注了篇名,还采用了新式标点。但是,除此以外,前面所举《辞源》的缺点、错误,在《辞海》中仍多存在,特别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二书有不少共同之处,读者查考时应当注意。《辞海》《辞源》二书收编的条目不尽相同,可相互参照,取其所长。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如杨树达的《词诠》、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朱起凤的《辞通》、符定一的《联绵字典》、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等等,至今也还有参考作用。 解放后,字典和词典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三十年来,先后编辑、出版了《新华字典》、《同音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汉语小词典》、《四角号码新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和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并开始新编《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此外,还有《辞源》、《辞海》的修订、改编。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学术界协作努力下,《辞海》(1979年版)已于1979年9月出版,精装三巨册。新版《辞海》收单字一四八七二个,复词九一七○六条,插图三千余幅,计一千三百余万字。这是一部百科性辞书,主要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在改编、修订过程中,除上述1979年的新版本外,从1961年起,《辞海》还曾印刷过四种本子:(1)《辞海·试行本》,1961年出版,按学科编排,平装十六册,附总词目一册。(2)《辞海·试排本》, 1963年印,供征求意见用,按部首笔画编排,平装六十册,精装合编成三册。(3)《辞海·未定稿》,1965年出版,按部首笔画编排,精装二册。(4)《辞海》分册,按学科编排,共廿分册,装订成廿八本,分两种版本:“修订稿”,已出版廿三本,1980年出齐;“修订本”已出六本。 《辞源》的修订定稿工作也于1979年完成,共四个分册,将于1981年出齐。修订后的《辞源》是一部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供文史研究工作者参考。收词限于古典文史范围,而且一般止于鸦片战争;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全部新词则一律删去。单字下注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并加《广韵》(间采《集韵》等)的反切,标出声纽。释义简明确切,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及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全部书证加注了作者、篇目和卷次,有些条目之末还附了参考书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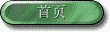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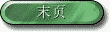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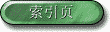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