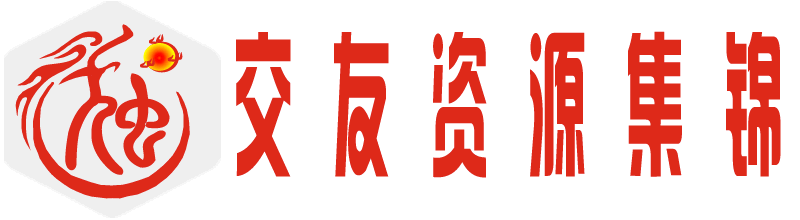★《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29–59 研究論文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譚躍、郭莘摘要近年來交友軟體興起,其於行動載具使用、可匿名性、私訊互動、地點配對的使用特性為青少年帶來社交便利,也伴隨著風險。基於使用與滿足理論,本研究欲探討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的動機、社交風險行為及其調節因素(家長介入行為、青少年年齡、性別和自戀程度)。本研究透過在青少年常常拜訪的網站上張貼連結的便利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在 2018 年 4 至 5 月期間共回收 512 份 15–17 歲青少年的問卷。其中 473 位曾經在過去一年使用過交友軟體,本研究以此族群的問卷資料作為分析資料。研究結果發現:(1)多數的青少年不常使用交友軟體。(2)打發時間、好奇與交友是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的主要動機。(3)青少年最常面臨的社交風險為暴露個人信息。(4)生理和社交動機可以直接增加社交譚躍,國立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副教授。研究興趣:媒介效果、災難風險傳播、政治傳播。電郵:yuetan@mail.nsysu.edu.tw郭莘,國立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研究興趣:社交媒體研究。電郵:s410074238@gm.ntpu.edu.tw論文投稿日期:2019 年 7 月 10 日。論文接受日期:2020 年 3 月 16 日。30《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風險,同時生理動機還可以透過使用交友軟體間接增加社交風險。(5)指導型家長介入行為只能降低娛樂動機引起的使用頻率。關鍵詞:使用與滿足、交友軟體、社交風險、青少年、家長介入行為Research Article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8 (2021), 29–59Mobile Dating Apps Uses by Adolescents:Motivations, Social Risks, and ModeratorsYue TAN, Hsin KUOAbstractMobile dating applications have increased in popularity among adolescentsin recent years, which has exposed them to various types of social risks. Basedon 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this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themoderators of the effects of adolescents’ motivations for using mobile datingapps on their social risks. In this study, an online survey was disseminatedthrough popular websites among adolescents in April and May 2018. Theparticipants included 512 adolescents aged 15 to 17 years. Among them, 473had used mobile dating apps at least once in the previous year, and theirresponses to the questionnaire provided the data used in the analysis. Thesurvey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of the adolescents in this study did not usemobile dating apps frequently. Killing time, curiosity, and making new friendswere the strongest motivations. Among various types of social risks, theadolescents most often disclosed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Both physical andsocial needs directly enhanced social risks. However, only physical motivationindirectly influenced social risks through the usage of mobile dating apps.Yue T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National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effects, disaster and risk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Hsin KUO (MA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National Sun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social media.32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8 (2021)Instructive parental mediation can only decrease the usage of mobile datingapps caused by entertainment motivation.Keywords: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mobile dating applications, socialrisks, adolescents, parental mediation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Tan, Y., & Kuo, H. (2021). Mobile dating apps uses byadolescents: Motivations, social risks, and moderators. Communication andSociety, 58, 29–59.33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緒論台灣教育部 2015 年學生網路使用情形調查報告指出,93.3% 的台灣高中職學生擁有智慧型手機可輕易下載使用交友軟體;在 2016 年,交友軟體 Goodnight 用戶 15 萬人,主要使用者年齡為 16–24 歲。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的調查指出:92.8% 的台灣青少年在 2016 年曾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或網路社群分享生活、尋求認同和結交朋友。青少年通過行動載具能輕易接觸各種交友軟體,卻增加了家長監控的難度。青少年正處於自我探索、增強社會獨立性和逐漸轉變成獨立個體的階段(Kelly, 2001)。雖然青少年普遍視網路交友為機會,但交友過程中可能存在各式各樣的騷擾,甚至延伸成現實中的犯罪行為。隨著網路犯罪數量增加,考量青少年的自制力與判斷能力尚未發展完全,在諸多青少年可能遇到的網路風險中(例如接觸到暴力、色情、霸凌等不利於身心發展的內容),學者、家長與執法者最為關心的網路風險就是網 路 交 友 的 風 險(Cookingham & Ryan, 2015; Livingstone & Helsper,2008; Liu, Ang, & Lwin, 2016)。交友媒體作為新興的媒介,相關研究比較少,且多是西方對成年人的研究,以青少年作為研究對象的更是寥寥無幾。使用者的年齡發展階段會導致個人特質和個體需求的差異(Timmermans & De Caluwé,2017)。青少年使用網路媒介的需求可能與成人不同。網際網路早已成為台灣青少年接觸色情內容的最主要管道,以及影響他們性態度、性行 為 和 強 暴 迷 思 的 重 要 因 素(羅 文 輝、吳 筱 玫、向 倩 儀、劉 蕙 苓,2008)。但青少年藉助行動載具使用性內容對其性發展(特別是性行為)的影響的研究卻還非常稀少,是當前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Aubrey& Gamble, 2017)。交友軟體具有於行動載具使用、可匿名性、私訊互動、地點配對等使用特性,很可能增加青少年的社交風險:例如在行動載具使用交友軟體使青少年能在脫離家長的管控下使用;可匿名性讓使用者能隱蔽自己的身分;私訊互動提供了青少年洩漏自己資訊的管道;地點配對則讓青少年能夠輕易與附近網友見面。雖然目前有不少交友軟體都34《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帶有未成年人使用的保護功能,將註冊門檻設置為 18 歲。但青少年只要謊報年齡就可以輕易的通過審核。因此,交友軟體對青少年造成的潛在社交風險值得探討。相對而言,青少年對據實填答問卷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顧慮,造成相關研究收集資料的難度。由於網路媒體允許青少年自主選擇多樣性的內容,使用與滿足理論特別適合考察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的整個過程,包括使用動機、使用過程和使用結果。本研究除了透過青少年社會及心理的需求考察青少年不同類型交友軟體使用的原因,也填補青少年在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上的研 究 缺 口。另 外,本 研 究 還 呼 應 學 者 們(Katz, Blumler, & Gurevitch,1974)的警告,媒體使用不但可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還有很多使用者未曾預料的其他結果。為此,本研究同時考察使用交友軟體會導致青少年暴露於哪些社交風險行為,這是青少年使用者未曾關注的重要後果。基於使用與滿足理論,在控制了青少年的個人和家庭因素之後,探討的研究問題包括青少年在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過程中都遇到哪些風險?這些風險與以往有哪些不同?青少年為什麼會選擇使用移動交友軟體?並出於哪些使用動機?不同類型的動機(如:生理需求、社交需求、好奇心、娛樂)對使用頻率的影響為何?青少年不同類型的動機是否都會透過長時間使用,最終產生社交風險行為?或是某些動機可以直接導致風險行為?家長介入青少年使用是否可以降低青少年動機對社交風險的影響?文獻探討移動交友軟體上的社交風險使用網路會遇到各種類型的風險(Natascha & Peter, 2014)。網路風險行為是指相對於其他「安全」的網路使用行為,會讓使用者接收到負面回饋的行為(Koutamanis, Vossen, & Valkenburg, 2015)。過去研究將網路風險行為分成許多類別。Lenhart 和 Madden(2007)將網路風險行為分成看到色情圖片、網路霸凌、發出/接收性相關訊35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息、與網友見面與其他等五種類型。後來的研究者陸續加入新的風險行為,例如結交網友、揭露個人訊息給網友、設網友為好友、偽裝身分(Natascha & Peter, 2014)、與 網 友 有 性 相 關 談 話(Branley & Covey,2018)。林淑芳(2016)則將各種具體的風險行為概況為內容風險、接觸風險和商業風險。移動交友軟體(mobile dating application)是指在行動裝置上的約會/交友軟體,在台灣多稱為交友軟體,因此本研究沿用該名稱。交友軟體在行動載具使用、可匿名性、私訊互動、地點配對的主要特性(David &Cambre, 2016),使青少年更容易接觸到網路風險行為,特別是透露出自己的個人資訊,甚至在現實見面,增加了遭遇風險的可能(Livingstone& Helsper, 2008)。首先,在行動載具上使用的特點,讓青少年可以隨時隨地使用交友軟體,脫離家長的監視與管理(Symons, Ponnet, Walrave, & Heirman,2017)。青少年在行為決策時著眼於眼前的利益而非長遠的規劃,容易忽視行為背後所潛藏的風險(Albert & Steinberg, 2011),若獨自使用交友軟體且無旁人給予意見時,較可能會進行網路風險行為。交友軟體可匿名的特性,利於使用者在交友軟體中偽裝身分,創造虛擬的身分,包含性別、種族、年齡等(Helen, 2006),甚至能偽造婚姻狀態、放假照片等。判斷能力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不足以分辨對方的真實資訊和身分。交友軟體與社群網站有部分相似處,使用者能選擇性揭露個人資訊,透過供人閱覽自己創造的個人檔案,與他人建立連結。但與社群網 站 不 同 之 處 是 交 友 軟 體 所 建 立 的 連 結 往 往 是 一 對 一 的 私 人 互 動(Ward, 2017)。因為青少年普遍還未養成隱私意識,這樣的私訊方式為他們提供了透漏自己個人資訊的新管道(Van Gool, Van Ouytsel, Ponnet,& Walrave, 2015)。除此之外,交友軟體多綁定定位服務功能(location-based services)。定位服務功能是提供使用者位置資訊的網路服務,多應用在移動裝置的軟體上(Kim, 2016),交友軟體往往需綁定此服務以提供使用者對所在地點附近的其他使用者進行交友配對的服務。交友軟體篩選了網友的可能所在地,讓青少年能更輕易地從線上交友延伸至線下,與所在36《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地附近的網友見面,增加了「與網友見面」的可能(Courtney, Jeremy, &Charles, 2014)。綜上所述,交友軟體的四個新特性創造了新的使用動機和新的「網路風險行為」,這是過去的「風險」研究未曾考察的。因此本研究參考過去研究,針對交友軟體的特性,對網路風險行為進一步聚焦,歸納出使用「交友軟體」此一媒介時所可能的風險行為,並將之稱為「社交風險」。交友軟體社交風險的主要特徵是使用者與陌生網友的彼此認識是起源在行動載具的交友軟體上,透過可匿名和私訊的互動,往往發展為實際的見面、兩性交往,甚至性行為。這些特徵本身是一個過程,包括使用的行為,也包括使用的結果。對一般人來說,稱之為風險的主要原因在於其中可能有虛假和欺騙的行為,也有可能發展出超過一般社會倫理的兩性關係。對青少年而言,除此之外,還可能阻礙他們完成其成長所必須的其他重要任務,例如課業學習(Nikken, 2017)。美國過去 10 年的調查資料顯示有接近一半的高中生曾從事過性行為,且呈緩慢上升的趨勢。美國國家兒童健康和人類發展部很早就委託學者調查發現媒體使用是青少年性行為的重要危險因子。青少年一方面透過模仿學習性行為,另一方面被媒體中所描繪的無負面結果的性 娛 樂 所 涵 化,高 估 同 儕 中 從 事 性 行 為 的 比 例(Aubrey & Gamble,2017)。越多觀看電視中性內容的青少年,越早開始性行為,越有可能懷孕或造成對方懷孕(Chandra et al., 2008)。從心理層面看,觀看媒體中的性內容還會造成青少年低落的性自我形象,例如:性自尊低、性自主性低、性焦慮高等(Aubrey, 2007)。羅文輝等人(2008)調查台灣的高中生發現,在各種色情媒介中,青少年收看比例最高的是網路色情。此外,網路色情的收視頻率與從事互動性網路色情活動的頻率,是預測青少年性態度、性行為與強暴迷思的顯著變項。針對青少年使用者從事這些風險行為的頻率,本研究將回答第一個研究問題 RQ1:青少年在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過程中都遇到哪些風險?頻率為何?過去研究顯示網路使用頻率會正向影響網路風險行為(Livingstone & Helpsper, 2008)。Best、Manktelow 和 Taylor(2014)進 一步指出青少年花在社交媒體上的時間越多,越有可能成為網路霸凌的受害者。無論是使用網路或是社交媒體的研究文獻都發現接觸媒介的37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時間正向影響遭遇網路風險的機率。Subrahmanyam 和 Greenfield(2008)指出在網路溝通中,頻繁的溝通頻率以及高度的自我揭露,都會加快與陌生人建立關係的速度。故本研究提出假設 1:H1:交友軟體使用頻率會正向影響社交風險。使用的動機:使用與滿足理論接下來,本研究要探討青少年為什麼會選擇使用移動交友軟體?根據使用與滿足理論,媒介使用決定於使用者的需求與動機、心理與社會環境、大眾傳播媒介、媒介使用的替代性、溝通行為等(Rubin,2002)。這些關鍵因素中,使用與滿足理論特別強調個體如何使用傳播媒介或其他型態的溝通方式滿足自己社會與心理的需求(Katz, Blumler,& Gurevitch, 1973)。使用與滿足理論假設媒介使用者是積極的、有目的和有選擇性的(Krcmar, 2017)。雖然這個假設在電視當道的時代遭到許多的挑戰,但在網路媒體多頻道多內容的時代,重新被學者青睞,被廣泛用於考察各種不斷更新的網路應用功能和媒介內容。使用與滿足理論對於理解人們為什麼選擇某個媒介和怎樣使用這個媒介提供了一個廣泛的視角,使研究者可以更好的理解包括選擇性接觸和媒介效果在內的整個媒體使用過程(Krcmar, 2017)。近年來,使用與滿足理論已被廣泛應用於社群媒體和即時訊息使用動機的研究(Cookingham & Ryan, 2015)。但很少研究特別針對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進行考察。早期的研究指出社交是青少年上網的主要動機,青少年將即時訊息 和 聊 天 室 視 為 能 發 展 和 維 持 社 交 關 係 的 管 道(Patti, Alexander, &Jochen, 2005)。隨著社交媒介的興起,「上網動機」已無法精確描述使用者選擇特定媒介的原因,使用網路可再細分為使用不同網路平台。根據功能論的假設,雖然閱聽人依據個人動機選擇不同的網路平台,但不同平台仍可能具有相似的功能和使用動機,因此過去對於成人使用交友軟體動機的研究對本研究仍具參考價值。Sumter、Vandenbosch 和 Lightenberg(2017)指出,對成人而言,交友軟體的使用動機能分成三個主要面向:生理需求(physical needs)、38《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社 交 需 求(social needs)和 其 他 社 會 心 理 需 求(psychosocial needs)。Timmermans 和 De Caluwé(2017)也指出使用交友軟體的動機除了社交需求外,還有娛樂和增加自信的需求。生理需求是指與「性」有關的需求。台灣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統計數據顯示,11.1% 的台灣青少年有性經驗,還不包含隱匿未報的部分。多數的媒體學者認為交友軟體的興起應歸功於易於發展性關係的功能(Mason, 2016)。過往研究顯示生理需求是使用者選擇使用交友軟體的主要動機之一,17% 的 Tinder 成年用戶藉由該軟體發展了一夜 情(Sumter, Vandenbosch, & Ligtenberg, 2017)。然 而 也 有 研 究 認 為用戶主要動機是尋求娛樂,而非為了發展伴侶關係或是尋找性伴侶(Timmermans & De Caluwé, 2017)。社交需求是指期望與他人互動並建立穩定關係的需求,與生理需求不同,社交需求主要尋求情感依附。Sumter(2017)等學者發現交友軟體使用者對於「愛」的動機比對於「性」的動機強烈。尤其是當人們處於青少年階段時,會開始好奇並嘗試發展伴侶關係,並且想引起他人注意(Steinberg, 2005)。青少年對浪漫關係的渴求也是使用社交媒體的主 要 動 機 之 一(Choukas-Bradley, Goldberg, Widman, Reese, & Halpern,2015)。交友軟體沒有朋友圈的設定,多為一對一認識,因此對象多為認識線上線下沒有任何已知連接關係的新朋友,這種情形既提供極佳的社交機會,也增加社交風險。其他的需求還包括好奇心、追隨潮流、打發時間、增加自信等多種需要(Bartsch, 2012)。交友軟體滿足了對未知事物的探索、使用新產品的好奇心。好奇心也是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的重要動機之一(Lai &Yang, 2014)。這些「好奇」與尋求娛樂的動機使想交友的人,從使用傳統的約會網站進而嘗試使用交友軟體(Giulia & Christoph, 2016)。此外,尋求娛樂的需求促使人們使用社群媒體,從中尋求刺激與快感,還會影響部分追求高度感官刺激的使用者,最後可能發展成一夜情(Baumgartner, Sumter, Peter, & Valkenburg, 2012)。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想要考察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綜上所述,過去 Sumter 等人(2017)的研究發現大學生使用 Tinder的動機主要為:生理需求、娛樂需求和社交需求。使用動機越強烈39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者,使用的頻率也會越高。因此本研究好奇青少年使用者是否具有這三方面的動機,哪種動機最強烈?哪種動機對使用頻率和社交風險的影響最大?為此,本研究考察以下研究假設:H2: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會正向影響使用頻率。具體而言,使用者的生理需求(H2a)、娛樂需求(H2b)和社交需求(H2c)越高,使用交友軟體的頻率就越高。H3: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會正向影響社交風險。具體而言,使用者的生理需求(H3a)、娛樂需求(H3b)和社交需求(H3c)越高,所從事的社交風險行為的頻率就越高。接下來,本研究想考察研究問題四:青少年不同類型的動機是否都會透過長時間的使用移動交友軟體,而最終發展成為風險使用行為?或者完全不需要使用時間作為中介,動機直接就造成風險使用行為?根據前文,提出以下假設:H4:交友軟體使用頻率會完全或部分中介使用動機對社交風險的影 響。具 體 而 言,交 友 軟 體 使 用 頻 率 會 完 全 或 部 分 中 介 生 理 需 求(H4a)、社交需求(H4b)和娛樂需求(H4c)對社交風險的影響。家長介入行為家庭對個體的社會化過程相當重要,過去研究指出家庭會影響青少年網路使用與網路風險(Kabasakal, 2015)。無論是傳統媒體或是新媒體,家長都被認為是影響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的主要社會因素。家長在子女的社會化階段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孩子會通過與家長的互動習得社會規範,並模仿其價值觀;家長也會保護小孩,讓他們遠離可能的危險(Grusec & Hastings, 2014),其中包括使用網路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青少年的父母被認為是媒介使用風險和收益的主要促成者、老師和守門人(Nikken, 2017)。家長的介入行為(parental mediation)是指家長針對子女媒介使用行為所進行的控制、管理行為(王嵩音,2016)。過往文獻將家長的介入行為分為限制型介入與指導型介入(Lwin,Stanaland, & Miyazaki, 2008; Chen & Chng, 2016)。限制型介入是指家40《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長限制孩童的使用時間、閱覽內容,並且制定使用規則;指導型介入則是家長與孩童溝通如何使用媒介,並且討論媒介內容,或是陪孩童一起使用。這兩種家長介入行為也是研究中最常被比較的兩種家長介入行為方式(林淑芳,2016)。家長介入也是過去文獻考察如何降低青少年觀看電視性內容對其性 態 度 和 性 行 為 的 負 面 效 果 的 一 個 研 究 重 點(Aubrey & Gamble,2017)。Fisher 等學者(2009)發現限制型介入對干預青少年性行為最為有效,特別可以減少他們從事口交和性交的可能性。但是文獻中,關於家長指導型介入對青少年性行為的干預效果的研究發現卻常常不太一致。交友軟體的特性似乎讓家長的介入更難以發揮成效:行動載具可以使青少年脫離家長的監視,可匿名性可使青少年隱藏未成年的身分,私訊互動讓青少年與網友的互動情形難以得知,地點配對則降低了青少年與網友見面的難度。根據過去文獻(王嵩音,2016;Nikken,2017):指導型介入能夠提高青少年自律性,降低使用頻率;限制型介入能夠規範青少年的交友軟體使用行為,也會減少使用頻率,本研究作出以下假設:H5:家長介入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方式和頻率可能會降低青少年交友軟體的使用頻率,即(H5a):家長限制型介入程度越高,青少年交友軟體的使用頻率就越低;以及(H5b):家長指導型介入程度越高,青少年交友軟體的使用頻率就越低。另外,相關的研究問題為 RQ2:哪種家長介入方式(限制型還是指導型)可以比較有效地降低青少年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使用頻率和社交風險使用的影響?個人因素的控制:性別、年齡與自戀程度使用與滿足理論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就是考察哪些個人特徵影響媒介的使用動機、使用行為及其關係(Krcmar, 2017)。在諸多的個人特徵中,人格特質是最重要的研究變項之一。人格特質是指個人外在41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行為表現的內部原因和屬性。它是人和人之間差別的最重要指標,也是 媒 介 選 擇、媒 介 偏 愛 和 媒 介 效 果 最 重 要 的 前 置 變 項 和 調 節 變 項(Timmermans & Sparks, 2017)。隨著社群媒體的興起,國內外很多研究都開始考察人格特質對社群媒體使用與滿足的影響。例如,Fox 和Rooney(2015)發現自戀程度高的人更喜歡使用社群媒體和發佈自拍照,花更長的時間編輯照片。研究者還發現年輕世代的自戀分數顯著高於過去的世代,並將這個差異歸因於智慧型手機和社群媒體的廣泛使用(Timmermans & Sparks, 2017)。自戀(narcissism)是一種人格特質,喜歡誇大自我概念、自我重要性和期待被人戀慕(Buffardi & Campbell, 2008)。很多研究發現自戀程度與線上自我資訊的揭露以及社交活動呈現正相關(Liu et al., 2016)。高自戀程度者通常會較為專注在自己身上,以自己的感覺為優先,並且認為自己較其餘人優秀(Leung, 2013)。研究顯示高自戀程度的個體傾向於揭露更多個人資訊,公開對自己有利的資訊以強調個體優勢。他們偏好分享具吸引力的自拍照片和吸引人的資訊,獲取他人的目光,能選擇性展現自己的社群網站便是他們最佳的舞台(Kim & Chock,2017; Leung, 2013)。自戀程度高者對於與他人建立深度的關係興趣較低,比起需要投入情感的面對面的朋友,他們傾向於認識更多社群網站上的朋友,以獲 得 大 眾 關 注 及 讚 許,滿 足 虛 榮 心(Davenport, Bergman, Bergman, &Fearrington, 2014; Leung, 2013)。過去研究顯示青少年的性別與年齡會影響網路使用頻率以及網路動機。英國孩童網路使用行為調查顯示,以性別而言,男孩較女孩傾向使用網路認識朋友,以年齡而言,年長的青少年比年幼的青少年更可能使用網路認識朋友(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在使用動機的部分,成長中的青少年會逐漸增加對於愛以及性的需求,並尋求親密關係,隨著年紀增大,使用者愛與性相關的交友動機就越強烈(Sindy, Patti, & Jochen, 2013; Sumter et al., 2017)。不同性別的網路使用動機也會有所差異,研究顯示男性比女性較常使用網路尋找潛在的性伴侶(Gatter & Hodkinson, 2016; Valkenburg & Peter, 2007)。42《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綜上所述,青少年使用者的自戀程度、性別和年齡都有可能影響他們使用交友軟體的動機和行為,因此在檢驗前文的研究假設時,被列為控制變項。除此之外,本研究還納入若干其他控制變項,包括家長收入、家長教育程度與家庭結構。過去研究指出家長的受教育程度和 收 入 越 高,青 少 年 使 用 網 路 的 比 例 顯 著 較 高(Jung, Kim, Lin, &Cheong, 2005)。因它們可能對研究造成影響,故納入控制變項。Livingstone 和 Helsper(2008)指出家庭結構會影響孩童的網路風險行為。結構完整的家庭能夠提供解決問題的功能、角色溝通功能、表達情緒功能、成員彼此互相關心和行為控制功能(Kabasakal, 2015)。反之,來自父母離異家庭的青少年,由於缺少社會支持,較有可能轉而向網路尋求與陌生人的關係以及連結(Wells & Mitchell, 2008)。即單親家庭的青少年相對於雙親家庭的青少年,更傾向使用網路社群認識新朋友(Lenhart & Madden, 2007),因此納入家庭結構作為控制變項。研究方法研究架構與對象本研究架構以交友軟體使用動機為自變項;交友軟體使用頻率為中介變項;社交風險行為作為應變項;家長介入行為作為調節變項;青少年的性別、年齡、自戀程度、家庭收入、家庭結構和家長教育程度作為控制變項。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使用交友軟體的青少年。青少年可以被分成12–15 歲 的 早 期 青 少 年 與 15–17 歲 的 晚 期 青 少 年(Koutamanis et al.,2015)。根據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2017 年對青少年的調查研究報告(張卿卿、陶振超,2018),98.4% 的台灣高中職生擁有僅限自己使用的能下載交友軟體的智慧型手機,顯著高於國中小階段的青少年。高中職生年齡介於 15–17 歲,正是擁有較成熟的性發展、自主性,脫離家長、老師管教的時期。故本研究以 15–17 歲的高中職生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本文研究所針對的媒體為交友軟體,因此選擇從 IOS App Store 台灣區以及 Google Play 社交類別下載排行榜前五十名中選擇符合上述特性的交友軟體(Goodnight、BeeTalk、Pairs、JustDating、Paktor、緣圈、43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Skout、wootalk)進行研究。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曾使用過 Goodnight、BeeTalk、Pairs、JustDating、Paktor、緣圈、Skout、wootalk 中任一軟體的 15–17 歲青少年。本研究採用網路調查法。網路調查法除了效率高且成本低廉,更重要的是具匿名性特點。當問卷涉及較敏感的議題,匿名性可能會提高受訪者的作答意願。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2017 年對成人的問卷調查研究發現自填組所填報的使用交友軟體的頻率顯著高於面訪組(張卿卿、陶振超,2018)。本研究在 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2018 年 5 月 14 日,於 Facebook、批踢踢及各交友軟體發放問卷,共計回收 473 份有效問卷。完成問卷填答者可獲得 Line 貼圖或 P 幣(網路虛擬貨幣)等作為獎品,增加填答意願。在性別部分,女性樣本數(53.3%)略多於男性(46.7%)。在年齡部分,15 歲青少年佔 39.2%,16 歲青少年佔 39.6%,17 歲青少年數量最少,佔21.2%。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屬於非隨機樣本,所有的被調查者都是交友軟體的使用者。目前文獻還沒辦法確定交友軟體的使用者佔全國高中生樣本的實際比例。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2017 年對青少年進行的問卷調查僅有一題涉及交友軟體的使用,即有 13% 的高中職生(n = 686)報告最常上網找或看的內容是交友軟體。這群人有 56.2% 是男生,大部分 16 歲(61.8%),其次是 15 歲(23.6%)和 17 歲(14.6%)。相較之下,本研究樣本的女生比例偏高,年齡分配比較平均。研究變項之操作性定義Ⅰ.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本研究將使用動機分類為生理需求、社交需求與娛樂需求(Sumteret al., 2017)。生理需求是指與「性」有關的需求;社交需求是期望與他人互動並建立一段穩定關係的需求;娛樂需求是指好奇心、追隨潮流、打發時間等心理需求(Bartsch, 2012)。測量題項基於 Timmermans 和 DeCaluwé(2017)的 研 究,並 參 考 相 關 研 究(Mason, 2016; Sumter et al.,2017),使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共 17 個題目,具體題項內容參考附錄。收集資料後,將各需求的題項分數分別加總。由於過去尚未有將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分類的研究,本研究對使用動機的分類進行驗證性44《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因素分析,力求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分類的信效度。CFA 的結果顯示,以三個構念為潛在變數,各題向的 CR 與 AVE,CR 皆高於 .6,AVE 皆大於 .5,整體而言,本量表具有聚斂效度。使用動機中的娛樂好奇動機原本有 5 題,信度較低(Cronbach’s α = 0.646 < 0.7)。當將題項「我的朋友們都在使用」刪除後,信度提高至 0.791。性需求和社交需求的信度(Cronbach’s α = .94 和 .90)也顯示良好。Ⅱ. 社交風險行為基 於 過 去 研 究(Branley & Covey, 2018; Courtney et al., 2014;Rodríguez-de-Dios, Oosten, & Igartua, 2018),考 慮 交 友 軟 體 的 使 用 特性,並且概括公眾所關心的風險情況,本研究將交友軟體中社交風險行為的操作性定義為從事 10 種具體風險行為的頻率的總和,題項內容列在表一。請受訪者按照「從來沒有」、「很少」、「有時」、「經常」分別給予 1 至 4 分。量表信度良好(Cronbach’s α = .87)。Ⅲ. 交友軟體使用頻率衡量青少年去年一年內,平均每週使用交友軟體的次數。基於王嵩音(2016)的網路使用頻率調查,將使用頻率的選項訂為「每天一次(或一次以上)」、「每週兩、三次」、「每週一次」、「每月一、二次」、「兩、三個月一次」、「半年一次」、「一年一次」,並分別給予 7 至 1 分,分數越高代表使用頻率越高。Ⅳ. 家長介入行為過去的相關研究主要將家長介入行為分為限制型介入和指導型介入(Chen & Chng, 2016)。基於過去的相關研究(Chen & Chng, 2016; Liu etal., 2016; Rodríguez-de-Dios et al., 2018; Shin & Kang, 2016),本 研 究 整理出適當的題項敘述。限制型介入和指導型介入各五題。其中限制型介入的題項分別為:(1)家長會規定我使用手機的時間;(2)家長會在一旁監視著我使用手機;(3)家長會規定我與網友的互動界線;(4)家長會限制我能下載的 App;和(5)家長會檢查我與網友的聊天記錄。45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指導型介入的題項分別為:(1)家長會告訴我可以分享與不能分享的資訊;(2)家長會解釋分析交友軟體的優點與缺點;(3)家長會教導我如果網友令我困擾我該如何解決;(4)家長會推薦我適合我年紀的App;和(5)家長會與我討論網路交友相關資訊與新聞。參考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題項的測量尺度設為「從來沒有」、「很少」、「有時」、「經常」,並分別給予 1 至 4 分,將題項加總後得到家長介入行為程度。本研究也對家長介入行為的分類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考察其構念效度,即相應的 5 個題項是否同屬一個構念。結果發現,10 個題項產生 2 個因素,5 個題項順利收斂到所屬的介入類型,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都高於 0.73,累積解釋變異量高於 63%。另外,限制型和指導型的量表的信度分別為(Cronbach’s α = .84)和(Cronbach’s α = .86)。以上結果顯示兩種介入類型的操作性定義信效度良好。Ⅴ. 控制變項:家長收入、家長教育程度和家庭結構根據 Leung(2013)對自戀的定義,本研究定義自戀為:將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以自我優先。其特質包含活在當下、依賴他人的目光、害怕依賴關係、極具自信。本研究參考 Raskin 和 Hall(1979)自戀人格量表(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和 Leung(2013)修改後的自戀人格量表,使用 10 個題項,內容分別為:我是個優秀的人;我是個天生的領導者;我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我喜歡當領導者;我喜歡被讚美;我喜歡成為焦點;我認為操縱別人是很容易的;我可以讓人相信我說的話;我喜歡看著我的身體;我喜歡照鏡子。使用李克特量表測量,受訪者的回答選項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分別從 1 分至 5 分,將題項的分數加總後即為自戀程度。量表信度良好(Cronbach’s α = .88)。由於青少年可能對於家庭經濟不甚清楚,因此參考過去以青少年為調查對象的調查的題目設計,將題項設為「很不富裕」、「不富裕」、「普通」、「富裕」、「很富裕」。家長教育程度以家長的最高教育程度為主,分為未受正式教育、小學、國中、高中/高職、專科、大學、研究所及以上。46《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家庭結構指的是家庭組成成員,分成單親、核心、祖孫、三代四種含括青少年的家庭組成方式。再將單親與祖孫家庭定義為家庭結構較不健全的結構,核心與三代家庭為較健全的組合。統計分析結果描述性統計參考附錄,青少年使用交友 App 的最主要動機為娛樂和好奇,其次是社交需求。一般青少年都不同意自己是出於性需求而使用交友軟體。在使用頻率部分,28.3% 的受訪者「一年一次」,是所佔比例最高的,其次則是「每天一次(或一次以上)」,佔 16.5%。在社交風險部分(表一),最常發生的風險行為是「告知網友自己的所在地」,次之為「與網友的談話中提及色情相關話題」。表一 社交風險行為的題項和因素的平均數和標準差題項 平均數(M)標準差(SD)社交風險行為(Cronbach’s α = .87) 1.99 0.66告知網友自己的所在地 2.38 0.89傳送自己的照片給網友 2.07 0.78洩露個人資訊 1.97 0.67與網友語音通話 2.08 1.07謊報資訊 2.11 0.90與網友視訊聊天 1.63 0.73與網友於現實見面 1.88 0.79在談話中提及色情話題 2.16 0.95與網友進行性行為 1.55 0.74告訴網友自己的聯絡方式 2.04 0.77在自戀程度部分,得分最高三題為:「我認為操縱別人是很容易的」(M = 3.06,SD = 1.11)、「我 喜 歡 看 著 我 的 身 體」(M = 3.05,SD =1.09)、「我是個天生的領導者」(M = 2.92,SD = 1.03);得分最低的三題47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為:「我喜歡被讚美」(M = 2.01,SD = 1.85)、「我可以讓人相信我說的話」(M = 2.39,SD = 0.94)、「我是個優秀的人」(M = 2.64,SD = 0.94)。受訪者 78.8% 來自於「核心與三代家庭」;「家庭收入」以「普通」最多(66.2%)。「父親教育程度」和「母親教育程度」都以「高中/高職」最多(35.7% 和 42.4%)。在限制型家長介入行為中,最常被使用的方法為「規定與網友的互動界線」(M = 1.66,SD = 0.94),次之為「規定使用手機的時間」(M =1.84,SD = 0.93);最 少 使 用 的 方 法 為「家 長 會 限 制 我 能 下 載 的 App」(M = 1.23,SD = 0.57)和「家 長 會 檢 查 我 與 網 友 的 聊 天 記 錄」(M =1.27,SD = 0.65)。在指導型家長介入行為中,最常被使用的方法為「告知可以分享與不能分享的資訊」(M = 1.91,SD = 1.06),次之為「討論網路交友相關資訊與新聞」(M = 1.74,SD = 0.95);最少使用的方法為「推薦適合年紀的 App」(M = 1.27,SD = 0.65),次之為「分析交友軟體的優點與缺點」(M = 1.44,SD = 0.82)。推論性統計Ⅰ. 預測交友 App 的使用頻率首先考察各變項對使用頻率的影響,階層迴歸第一階為控制變項:性別、年齡、家庭收入、家庭結構、家長教育程度,第二階為三種類型的使用動機:生理需求、社交需求、娛樂需求,第三階則將家長介入加入,結果呈現在表二。接下來主要報告的是第三欄中最後完整模型的結果。控 制 變 項 中 性 別(β = .112,p < .05)、年 齡(β = .096,p < .05)和家庭收入皆顯著(β = –.193,p < .001)預測使用頻率。男生、年紀越長,且越貧窮家庭的青少年越多使用交友 App。三種不同類型的動機,可 看 到 生 理 需 求(β = .218,p < .001)、社 交 需 求(β = .224,p <.001)對使用頻率都有正向影響。支持研究假設 H2a: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生理需求會正向影響使用頻率成立,和 H2b:交友軟體使用動機48《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中的社交需求正向影響使用頻率成立。同時,娛樂需求不能顯著預測使用頻率(β = –.002,p = .998),H2c 不成立。在迴歸分析之前,先將家長介入行為與交友軟體使用頻率進行兩兩相關分析,發現限制型家長介入行為與使用頻率無顯著相關(Pearsonr = –.051,p = .959);指導型家長介入行為與使用頻率顯著相關(Pearsonr = –.133,p < .01)。因此推論家長限制型介入與交友軟體使用頻率無關,H5a 沒有得到支持。但 H5b 預測家長指導型介入降低交友軟體的使用頻率暫時得到支持。為了避免家長限制型介入對家長指導型介入影響的分析,僅將家長 的 指 導 型 介 入 帶 入 迴 歸 分 析。因 兩 種 介 入 行 為 之 間 顯 著 正 相 關(Pearson r = .628,p < .001)。若將兩者同時帶入模型或者取平均數,有可能干擾或稀釋指導型介入對使用頻率的影響。表二階層三中新加入家長指導型的介入方式,結果顯示,它對使用頻率沒有顯著影響(β = –.075,p = .23)。因此,這個結果不支持研究假設 H5b,即家長指導型介入程度越高,使用頻率越低。總的來說,兩種家長介入方式,對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頻率都沒有顯著的影響。表二 各變項對使用頻率的影響(標準化迴歸係數)自變項 階層一β 值階層二β 值階層三β 值性別 .14* .133* .112*年齡 .11* .10* .096*家庭收入 –.21*** –.188*** –.193***家長教育程度 –.051 –.026 –.028家庭結構 –.042 –.029 –.047生理需求 .191*** .218***社交需求 .23*** .224***娛樂需求 .008 –.002家長指導型介入 –.075F 10.734*** 16.500*** 12.794***Adjusted R 平方 .15 .205 .210註:男 = 1,女 = 0;*< .05, **< .01, ***< .00149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Ⅱ. 預測交友 App 的風險接下來考察各變項對社交風險的影響。如表三所示,階層一控制變項中的性別(β = .159,p < .001)和自戀程度(β = .097,p < .05)顯著對應較高的社交風險行為。男性相對於女性,自戀程度高的人,較多從事社交風險行為。階層二加入三種不同類型的動機,可看到生理需求(β = .442,p <.001)、社交需求(β = .172,p < .001)對社交風險都有正向影響。H3a和 H3b 分別預測使用交友軟體的生理需求和社交需求會正向影響社交風險,被驗證為成立。但 H3c 預測娛樂需求正向影響社交風險的假設不成立。階層三加入使用頻率,發現使用頻率(β = .266,p < .001)對社交風險有顯著影響。這說明,H1 預測交友軟體使用頻率會正向影響社交風險也獲得支持。在階層三,帶入使用頻率後,社交動機的影響變為不顯著,暗示使用頻率完全中介社交需求對社交風險的影響。為驗證中介效果的統計顯著性,本研究以 SPSS Process 套件中的模型四(Model 4)進行中介效果(mediation)檢測(信賴水準 95%、模擬抽樣次數 5000)。發現生理需求(β = .079,CI:.054,.113)與社交需求(β = .111,CI:.211,.376)間接效果皆成立。此外,生理需求(β = .379,t = 10.823,p < .001)與社交需求(β = .293,t = 7.02,p < .001)對社交風險的直接效果也都顯著。由於間接效果與直接效果均成立,判斷為部分中介,故支持研究假設 H4a 和 H4b。由於娛樂需求對使用頻率和社交風險都沒有顯著影響,無法構成中介效果,因此研究假設 H4c 不成立。表三 各變項對社交風險之影響(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值)自變項 階層一 階層二 階層三性別 .188*** .172*** .159***年齡 .003 .002 .001自戀程度 .131* .112* .097*家庭收入 .022 .057 .104**家長教育程度 –.045 –.016 –.032家庭結構 –.069 –.045 –.041家長指導型介入 –.053 –.027 –.01350《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自變項 階層一 階層二 階層三生理需求 .442*** .393***社交需求 .172*** .08娛樂需求 .021 –.006使用頻率 .266***F 0.925 32.704*** 26.853***Adjusted R 平方 .006 .310 .406註:男 = 1,女 = 0;*< .05, **< .01, ***< .001結論與建議本研究以使用與滿足理論探討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使用和可能造成的社交風險,在控制了性別、年齡、自戀程度等干擾變項後,考察家長介入行為的調節作用,希望找出降低青少年因使用交友軟體而增加社交風險的因素,供相關決策者參考。本研究發現多數 15–17 歲青少年不常使用交友軟體,53.5% 的青少年僅偶一為之,但也有 16.5% 青少年每天使用一次或以上。現今大多數交友軟體下載年齡限制為 18 歲,但本研究發現過去一年至少使用一次的青少年非常多,本研究的有效樣本(n = 473)皆為未成年且曾使用過交友軟體的違規者,說明未成年而違規使用交友軟體的問題確實存在,其風險值得探討。在使用動機方面,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的主要動機為打發時間、好奇以及認識新朋友,他們都比較不認同自己是為了滿足性需求而使用交友軟體。這與 Giulia 和 Christoph(2016)認為好奇心會使人開始使用交友軟體的觀點相符。但另外一種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的樣本中大多數的青少年為輕度使用者。同時,研究結果顯示生理需求、社交需求與娛樂好奇動機都與交友軟體的使用頻率呈現兩兩關係的正向相關。但是同時考慮三種動機的時候,生理需求和社交需求對使用頻率的影響,不但遠遠高於娛樂好奇的影響,甚至可以抵消它的影響。正如 Giulia 與 Christoph(2016)研究所指出的,娛樂需求雖然可驅使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但難以成51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為後續持續使用的動機。同樣,生理需求、社交需求與娛樂好奇動機都與交友軟體的社交風險呈現兩兩關係的正向相關。但控制了生理需求和社交需求的影響後,娛樂好奇動機對社交風險行為同樣不具獨立的預測力。未來研究可繼續考慮因娛樂好奇動機而使用交友軟體和從事社交風險行為的青少年在個人特徵(性別、年齡、個性)和有效的家長介入方式上有怎樣不同的特徵,便於學校和家長預防和控制實際的社交風險。另外,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是考察哪種新傳播科技的特徵,容易引起青少年娛樂和好奇的動機。Sundar 和 Limperos(2013)歸納了四種新科技的符擔性(affordance):包括型態(modality)、能動性(agency)、互動性(interactivity)和通航性(navigability),他們為目前考察新媒體的使用與滿足提供了最好的理解方式(Krcmar, 2017)。另外,本研究發現性別和年齡都會直接影響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的頻率。男性的使用頻率與社交風險均高於女性。此外,性別會強化生理需求和社交需求對使用頻率的影響,表示男性更容易基於生理需求和社交需求增加交友軟體的使用頻率。年齡較長的青少年較多使用交友軟體,但不一定遇到較高的社交風險。本研究結果與英國孩童網路使用行為調查結果相符。本研究亦發現青少年年齡對社交需求與使用頻率的關係具調節效果。年齡較大的青少年更容易因為社交需求而使用交友軟體。年齡越大者,其對愛的渴求越高,更會使用交友軟體追求內心愛的滿足(Sindy et al., 2013)。年齡未對生理需求起到調節作用,可能是因為受訪者年齡為 15 至 17歲,此年齡區間的青少年對生理需求可能差異不大,而過往 Sindy 等人(2013)的研究是針對 12–17 歲青少年,其研究結果才會有年齡上的差異,發現年紀越大的青少年對於愛與性相關的需求就越高。本研究發現家長的指導型介入雖然可以降低使用頻率。但在控制了家庭因素、個人特徵和使用動機的影響後,家長的指導型介入的單獨解釋力便完全消失了。可能的原因是,家長的指導型介入僅對使用動機較弱的青少年有效,或者僅對於青少年以好奇娛樂為主要使用動機的時候有效。換句話說,如果青少年主要出於生理和社交需求使用52《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移動交友軟體,家長無法透過指導型介入有效地降低他們的使用頻率。未來研究可以繼續針對指導型介入有效的時機和範圍進行更全面的考察。家長介入的微弱效力與移動交友軟體具有於行動載具使用、可匿名性、私訊互動和地點配對的特性相關。特別是手機的高移動性,使家長無法有效介入(監督、指導、限制)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的行為。與指導型介入相比,台灣父母常常使用的限制型介入方式更是毫無效力。未來研究應該從決定青少年使用動機的個人特徵,或者從前面提到的科技符擔性下手,來尋找預測青少年交友軟體的使用行為和社交風險的重要因素,而非如傳統的固定媒體時代那樣,把責任和期待完全放在父母介入媒體使用的方法和強度上。除了交友軟體的使用,青少年的社交風險行為是本研究關注的另一個焦點。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對於線上活動較缺乏危機意識,常常提供個人資訊給網路上結識的朋友。大部分(52.9%)的受訪者都將線上關係延伸至線下,曾與網友於現實見面;31.3% 的受訪者甚至與網友進行過性行為。本研究發現生理和社交需求都是社交風險行為的有效預測因子,生理和社交需求越高,所作出的社交風險行為也越多。但娛樂好奇的需求不會導致社交風險行為。更重要的是本研究發現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的頻率正向提高社交風險行為。不但如此,中介分析的結果發現,交友軟體的使用頻率還會加強生理和社交需求對社交風險行為的影響。相對而言,生理需求對社交風險行為的直接效果比社交需求強,但社交需求對社交風險行為的間接效果比生理需求強。可能的原因是,交友軟體的使用不但表達和滿足了青少年的社交需求,還進一步增強了他們的社交需求,這符合 Sundar 和 Limperos(2013)的科技互動理論。結果還顯示青少年的自戀程度除了會正向提高社交風險,還會加強使用頻率對社交風險的正向影響。這個研究結果符合過去 Leung(2013)的觀點,自戀程度高的人喜歡分享自己的照片、使用網路進行交友等,而在其交友過程中,會不自覺地作出展示自我的風險行為。本研究建議相關單位加強宣導,告知青少年某些行為在獲得他人讚賞的同時也伴隨著社交危險,並針對因生理需求使用交友軟體的行53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為討論對應方式,例如加強性教育等,並且針對男性特別宣導交友軟體的風險行為。基於指導型介入行為在青少年因好奇娛樂動機使用交友媒體的情況下能降低使用頻率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建議家長採取指導型介入行為,比如分析交友軟體存在的優缺點、推薦適合青少年的App、告知青少年哪些資訊不該被分享,而非一味的限制與禁止。最後,本研究具有以下的幾個研究限制,日後的研究可以斟酌改進。首先,本研究屬於非隨機抽樣,且全部為交友軟體的使用者,年齡和性別與全台灣樣本可能存在差異,因此描述性統計的結果無法直接推論到全台灣青少年。Yin(2011)主張,個案研究方法的優點不是「人 口 描 述 性 的 概 括 性」,而 在 於「概 念 間 關 係 的 概 括 性」。 李 金 銓(2019:533)也指出小樣本內部差異的比較,雖不能過度推演,但因為具有概念的代表性,可以以小見大,看整體和部分的關係,看表面現象背後所表現的普遍規律。因此,本研究針對概念之間關係的推論仍然有效,也可以作為日後研究的參考依據。另外,本研究僅調查 15–17 歲青少年,但未來可增加不同年齡區間,尤其現今智慧型手機普及,部分國中生甚至國小生亦擁有行動載具能夠接觸交友軟體,其所形成的隱憂也須多加關注。最後,本研究的樣本中有 28.3% 使用頻率為一年一次。雖然社交心理需求的好奇心等動機較多影響這些較少使用的人,若只收集在固定使用交友軟體的樣本,對於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社交風險的影響,以及其他影響社交風險的因素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本研究對於個性特徵的考察僅限於自戀程度,未納入其他可能的個人特質,例如五大人格特質,未來相關研究可考慮納入。參考文獻中文部分(Chinese Section)王嵩音(2016)。〈家長介入行為影響青少年網路正負面使用行為之研究〉。《中華傳播學刊》,第 30 期,頁 31–59。Wang Songyin (2016). Jiazhang jieru xingwei yingxiang qingshaonian wangluzheng fu mian shiyong xingwei zhi yanjiu. Zhonghua chuanbo xuekan, 30,31–59.54《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李金銓(2019)。《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新北市:聯經出版社。Li Jinquan (2019). Chuanbo zongheng: Lishi mailuo yu quanqiu shiye. Xinbeishi:Lianjing chubanshe.林淑芳(2016)。〈青少年網路素養、家長介入、與網路使用經驗〉。《中華傳播學刊》,第 30 期,頁 3–29。Lin Shufang (2016). Qingshaonian wanglu suyang, jiazhang jieru, yu wanglushiyong jingyan. Zhonghua chuanbo xuekan, 30, 3–29.張卿卿、陶振超(2018)。〈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二期第一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5-2420-H-004-033-SS3)〉。取自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http://www.crctaiwan.nctu.edu.tw/AboutSurvey.asp。Zhang Qingqing, Tao Zhenchao (2018). Taiwan chuanbo diaocha ziliaoku di er qidi yi ci diaocha jihua zhixing baogao (Kejibu buzhu zhuanti yanjiu jihua,MOST 105-2420-H-004-033-SS3). Taiwan chuanbo diaocha ziliaoku.Retrieved from http://www.crctaiwan.nctu.edu.tw/AboutSurvey.asp.羅文輝、吳筱玫、向倩儀、劉蕙苓(2008)。〈網路色情與互動性活動對青少年形態與性行為影響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5 期,頁 35–69。Luo Wenhui, Wu Xiaomei, Xiang Qianyi, Liu Huiling (2008). Wanglu seqing yuhudongxing huodong dui qingshaonian xingtai yu xingxingwei yingxiangyanjiu.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5, 35–69.英文部分(English Section)Albert, D., & Steinberg, L. (2011).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in adolescence.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1(1), 211–224.Aubrey, J. S. (2007). Does television exposure influence college-aged women’ssexual self-concept? Media Psychology, 10(2), 157–181.Aubrey, J. S., & Gamble, H. (2017). Sexuality and sexual health: Media influenceon. In P. Rössler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media effects (pp.1–13). Malden, MA: John Wiley & Sons, Inc.Bartsch, A. (2012). Emotional gratification in entertainment experience. Whyviewers of movies and television series find it rewarding to experienceemotions. Media Psychology, 15(3), 267–302.Baumgartner, S., Sumter, S., Peter, J., & Valkenburg, P. (2012). Identifying teensat risk: Developmental pathways of online and offline sexual risk behavior.Pediatrics–English Edition, 130(6),1489–1496.Best, P., Manktelow, R., & Taylor, B. (2014). Online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and adolescent wellbeing: A systematic narrative review. Children and YouthServices Review, 41, 27–36.55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Branley, D. B., & Covey, J. (2018). Risky behavior via social media: The role ofreasoned and social reactive pathway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8,183–191.Buffardi, L. E., & Campbell, W. K. (2008). Narcissism and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10), 1303–1314.Chandra, A., Martino, S. C., Collins, R. L., Elliott, M. N., Berry, S. H., Kanouse, D.E., & Miu, A. (2008). Does watching sex on television predict teen pregnancy?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Pediatrics, 122(5),1047–1054.Chen, V. H. H., & Chng, G. S. (2016). Active and restrictive parental mediationover time: Effects on youths’ self-regulatory competencies and impulsivity.Computers & Education, 98, 206–212.Choukas-Bradley, S., Goldberg, S. K., Widman, L., Reese, B. M., & Halpern, C.T. (2015). Demographic and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 content andsequence of adolescents’ ideal romantic relationship behaviors. Journal ofAdolescence, 45, 112–126.Cookingham, L. M., & Ryan, G. L. (2015).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thesexual and social wellness of adolescents. Journal of Pediatric and AdolescentGynecology, 28(1), 2–5.Courtney, B., Jeremy, B., & Charles, A. (2014). Seeing and being seen: Co-situationand impression formation using Grindr, a location-aware gay dating app.New Media & Society, 17(7), 1117–1136.Davenport, S. W., Bergman, S. M., Bergman, J. Z., & Fearrington, M. E. (2014).Twitter versus Facebook: Exploring the role of narcissism in the motives andusage of different social media platform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2,212–220.David, G., & Cambre, C. (2016). Screened intimacies: Tinder and the swipe logic.Social Media+ Society, 2(2), 1–11.Fisher, D. A., Hill, D. L., Grube, J. W., Bersamin, M. M., Walker, S., & Gruber,E. L. (2009). Televised sexual content and parental mediation: Influences onadolescent sexuality. Media Psychology, 12(2), 121–147.Fox, J., & Rooney, M. C. (2015). The Dark Triad and trait self-objectification aspredictors of men’s use and self-presentation behaviors on social networkingsit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6, 161–165.Gatter, K., & Hodkinson, K. (2016).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inder™ versusonline dating agencies: Questioning a myth. An exploratory study. CogentPsychology, 3(1), 1162414.Giulia, R., & Christoph, L. (2016). Love at first swipe? Explaining Tinder self-presentation and motives.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5(1), 80–101.Grusec, J. E., & Hastings, P. D. (Eds.). (2014).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and research. NY: Guilford Publications.56《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Helen, K. (2006). Beyond anonymity, or future directions for internet identityresearch. New Media & Society, 8(6), 859–876.Jung, J. Y., Kim, Y. C., Lin, W. Y., & Cheong, P. H. (2005). The influence of socialenvironment on internet connectedness of adolescents in Seoul, Singapore andTaipei. New Media & Society, 7(1), 64–88.Kabasakal, Z. (2015). Life satisfaction and family functions as-predictors of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in university stud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53, 294–304.Katz, E., Blumler, J. G., & Gurevitch, M. (1973–1974). Uses and gratificationresearc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7(4), 509–523.Kelly, P. (2001). Youth at risk: Processes of individualisation and responsibilisationin the risk society.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22(1), 23–33.Kim, H-S. (2016). What drives you to check in on Facebook? Motivations, privacyconcerns, and mobile phone involvement for location-based informationsharing.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4, 397–406.Kim, J. W., & Chock, T. M. (2017).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predicting selfie posting behaviors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elematics andInformatics, 34(5), 560–571.Koutamanis, M., Vossen, H. G. M., & Valkenburg, P. M. (2015). Adolescents’comments in social media: Why do adolescents receive negative feedback andwho is most at risk?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3, 486–494.Krcmar, M. (2017).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Basic concepts. In P. Rössler (Ed.),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media effects (pp. 1–13). Malden, MA: JohnWiley & Sons, Inc.Lai, C. Y., & Yang, H. L. (2014).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Facebookfeature use. New Media & Society, 18(7), 1310–1330.Lenhart, A., & Madden, M. (2007). Teens, privacy and online social networks.Washington, DC: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Retreved from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07/04/18/teens-privacy-and-online-social-networks/.Leung, L. (2013).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content generation in social media:The roles of the gratifications sought and of narcissism. Computers in HumanBehavior, 29(3), 997–1006.Liu, C., Ang, R. P., & Lwin, M. O. (2016). Influences of narcissism and parentalmediation on adolescents’ textual and visual person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Facebook.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8, 82–88.Livingstone, S., & Helsper, E. J. (2008). Parental mediation of children’s internetus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2(4), 581–599.Lwin, M. O., Stanaland, A. J., & Miyazaki, A. D. (2008). Protecting children’sprivacy online: How parental mediation strategies affect website safeguard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Retailing, 84(2), 205–217.57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Mason, C. L. (2016). Tinder and humanitarian hook-ups: The erotics of socialmedia racism.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6(5), 822–837.Natascha, N., & Peter, N. (2014). Boys and girls taking risks online: A genderedperspective on social context and adolescents’ risky online behavior. NewMedia & Society, 18(6), 966–988.Nikken, P. (2017). Parental mediation of media. In P. Rössler (Ed.), The 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 of media effects (pp. 1–11). Malden, MA: John Wiley & Sons, Inc.Patti, M. V., Alexander, P. S., & Jochen, P. (2005). Adolescents’ identityexperiments on the internet. New Media & Society, 7(3), 383–402.Raskin, R. N., & Hall, C. S. (1979). A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PsychologicalReports, 45(2), 590.Rodríguez-de-Dios, I., van Oosten, J. M. F., & Igartua, J.-J. (2018). A study of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mediation and adolescents’ digital skills, onlinerisks and online opportuniti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82, 186–198.Rubin, A. M. (2002). The uses-and-gratifications perspective of media effects. In J.Bryant & D. Zillman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2nded., pp. 525–548).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Shin, W., & Kang, H. (2016). Adolescents’ privacy concerns and informationdisclosure online: The role of parents and the Internet. Computers in HumanBehavior, 54, 114–123.Sindy, R. S., Patti, M. V., & Jochen, P. (2013). Perceptions of love across thelifespan: Differences in passion, intimacy, and commitment.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7(5), 417–427.Steinberg, L. (2005).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development in adolescence. Trends inCognitive Sciences, 9(2), 69–74.Subrahmanyam, K., & Greenfield, P. (2008).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adolescentrelationships. The Future of Children, 18(1), 119–146.Sumter, S. R., Vandenbosch, L., & Ligtenberg, L. (2017). Love me Tinder:Untangling emerging adults’ motivations for using the dating applicationTinder.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34(1), 67–78.Sundar, S. S., & Limperos, A. M. (2013). Uses and grats 2.0: New gratifications fornew media.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7(4), 504–525.Symons, K., Ponnet, K., Walrave, M., & Heirman, W. (2017). A qualitative studyinto parental mediation of adolescents’ internet use. Computers in HumanBehavior, 73, 423–432.Timmermans, E., & De Caluwé, E. (2017). To Tinder or not to Tinder, that’s thequestion: 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perspective to Tinder use and motives.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10, 74–79.Timmermans, E., & Sparks, G. G. (2017). Personality traits: Influence on mediaeffects. In P. Rössler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media effects (pp.1–11). Malden, MA: John Wiley & Sons, Inc.58《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Valkenburg, P. M., & Peter, J. (2007). Who visits online dating sites? Exploringsome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dater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0(6),849–852.Van Gool, E., Van Ouytsel, J., Ponnet, K., & Walrave, M. (2015). To share or notto share? Adolescents’ self-disclosure about peer relationships on Facebook:An application of the Prototype Willingness Model. Computers in HumanBehavior, 44, 230–239.Ward, J. (2017). What are you doing on Tinder? Impression management on amatchmaking mobile app.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1),1644–1659.Wells, M., & Mitchell, K. J. (2008). How do high-risk youth use the Internet?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evention. Child Maltreatment, 13(3),227–234.Yin, R. K. (2011). Applications of case study research. Los Angeles, CA: Sage.本文引用格式譚躍、郭莘(2021)。〈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58 期,頁 29–59。59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附錄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的題項、平均數和標準差題項 平均數(M)標準差(SD)因素一:生理需求(Cronbach’s α = .94) 2.52 1.26尋找一夜情對象 2.42 1.36尋找無負擔的性行為對象 2.49 1.42尋找和我有一樣性癖好的人 2.54 1.61想試有多簡單找到性伴侶 2.51 1.36想增加性行為經驗 2.48 1.40想找人談論性相關話題 2.67 1.39因素二:社交需求(Cronbach’s α = .90) 3.17 0.95想尋找伴侶認真經營感情關係 2.77 1.28想與人約會 2.83 1.34想認識新朋友 3.5 1.13想與陌生人講話 3.33 1.21想擴大我的社交圈 3.2 1.2想與他人建立情感連結 3.09 1.23想增進我的社交技巧 3.47 1.06因素三:娛樂好奇動機(Cronbach’s α = .79) 3.54 0.85想打發時間 3.96 0.96因為好奇而使用 3.71 1.03朋友都在用,我也想用看看 ( 刪除 ) * 2.87 1.17只是隨便試用一下 3.33 1.13我沒別的事情好做 3.15 1.21註:*因為此題項與其他題項的一致性信度過低,故未加入該因素的計算 |